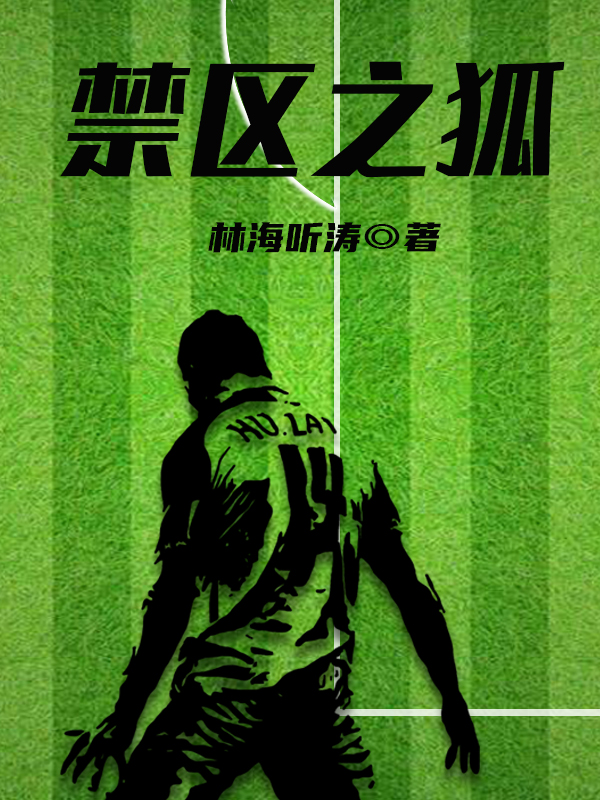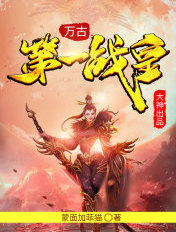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簪笔集陈悟 > 第101章VIP(第4页)
第101章VIP(第4页)
祝昭望向袁琢,而后对着莫踌笑了笑:“阿兄,我想与我夫君在此处向崔老先生和穆阿媪行个大礼,可以吗?”
莫踌惊讶,静默片刻才了然道:“原该如此的,先生夫人泉下有知,得见姑娘遇良人,必感欣慰。”
雨后的青石板泛着水光,两人相视一眼,齐齐望向了无生气的正堂。
二人并肩跪下,湿
泥立刻洇深了衣料,碎石硌在膝下,他们却跪得端正,三个头磕得虔诚。
“用一盏茶吗?”莫踌见二人起来了,又追问。
祝昭摇了摇头,眼角微微弯起:“阿兄,今日就不久坐了,改日再来。”
袁琢从袖中取出个油纸包递去:“泠君说你爱吃松糖,今日上街看到了便买了。”
莫踌微愣,接过了纸包。
祝昭向他行了一礼:“阿兄止步,过两日再来尝你的茶水。”
两人沿着湿滑的石阶渐行渐远,莫踌拿着松糖立在桂花树下,看那双身影转过溪弯。
深青与靛蓝的衣袂时而被风吹得交叠,像雨霁时分山峦与天的交界。
忽有呜咽的牧笛声飘来,一个骑在牛背上的牧童吹着笛子转出溪弯,与二人擦肩而过。
他无端地记起幼时在崔府时遇到的一个少年,只是那少年满身意气,崔老先生给他取了字,他也不知为何自己会想起那个只有几面之缘的少年,但那少年与方才的青年显然不是一人。
“听之。”
“嗯?”
“是崔老先生赠的?”
“是,我的字是他起的。”
“先前你说你的字是为老先生取的,我就有所怀疑了。”
“多谢。”袁琢停下脚步望向她。
祝昭也停下了脚步:“自我们重逢,你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多谢了,这次你要谢的又是什么?”
“多谢泠君让我全礼节。”
他目光似水,专注又长久地注视着她,下意识地回应。
“从前我迷茫难守之时,崔老先生常同我说莫要总困于一室之内,囿于一人之心,他让到各色各样的人中去,去观察,去观察他们的笑容,去观察他们的城府,老先生说唯有见得够多,听得够多,历经够多,方能真正明白人心的幽微复杂,明白世事的曲折难测,也方能更好地守住自己心里那一点或许不合时宜的东西。”
“你守住了。”祝昭望着他,苦涩地说。
她时常想,若是袁琢没有守住不合时宜的澄澈,成为了彻头彻尾的佞臣,会不会就不这么痛苦了。
可那一双透亮的眸子眼波潋滟,明晃晃地告知她,不会的,不会的,若是他没守住,那他就不是袁琢了。
祝昭叹了口气,袁琢听到她说:“那日听李校尉说到了我的日录,我的日录如何在你手中?”
“周涤周公子赠予我的。”
“周涤?”祝昭疑惑。
于是袁琢就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兼之周涤为何来徽州,如何得到日录的事情一一告诉了祝昭:“周公子来濯陵,恰巧途径你的小院,敲门不应,冒昧进门才发现屋主像是离开许久,于是他便暂住一宿,偶得《拾徽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