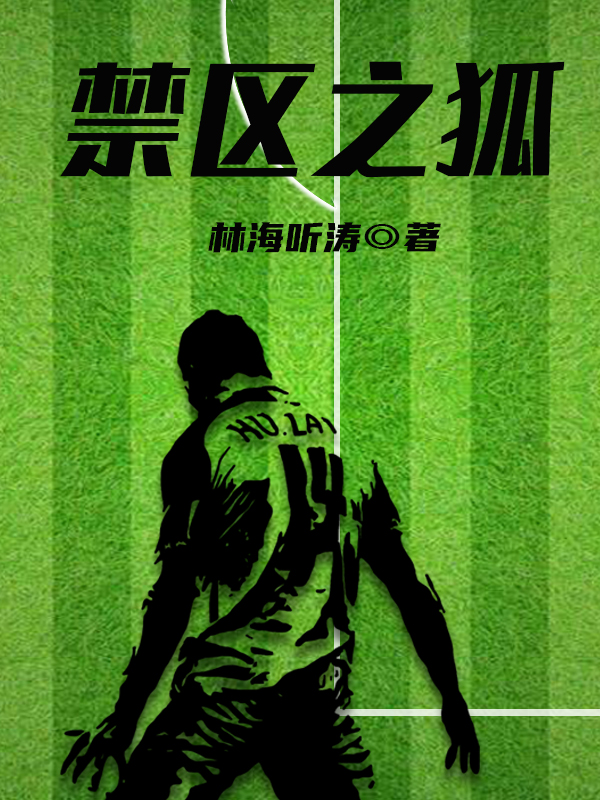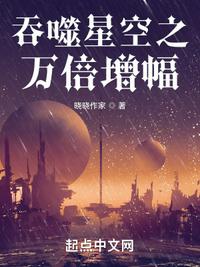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狼殿下演员表 > 第10章 鱼目岂能混珠(第3页)
第10章 鱼目岂能混珠(第3页)
她懂得他无声的体贴,并且感激他。
这几日,表面上两人处处水火不容,互看不顺眼,但到了临危关头,她竟有种错觉:朱友文会是她唯一的依靠。
再怎么样,他还是她未来的夫君,不是吗?
他总不会对自己未来的娘子落井下石吧?
皇宫大殿,处处藏着权谋心机,她什么都不懂,稍微说错一句话,也许面临的就是杀头,她并不怕死,她怕的是,自己死了,便再也无法替爹爹与马府全家报仇了!那是她至今仍愿意苟延残喘留着这条命的唯一理由啊!
她跟着朱友文的背影,来到了紫微宫,梁帝已上完早朝,正在朝阳殿等着两人,丞相敬祥、朱友珪也在殿上,其他还有杨厚等几位大臣。
人已到齐,梁帝开口问敬祥:‘丞相,听杨校尉说,他奉命前往相府调查时,那逃犯,已畏罪上吊自尽了?’
摘星与朱友文闻言皆是一愣,摘星更是于心不忍,面露哀伤。
尽管林广有所隐瞒,但她知道,老人绝不可能是什么刺客,况且丞相捉到人后,却没有送到刑部送审,而是带回自己的相府关押,犯人最后又上吊自尽,怎么看都是急欲想掩饰什么,透出蹊跷。
摘星忍不住望向朱友文,他察觉到她的视线,转过头,对她轻轻摇摇头,示意她先沈住气。
杨厚出声质问敬祥:‘丞相口口声声说那逃犯乃刺客,无凭无据,何以断定?还是其中另有隐情?’杨厚倒也不是胡乱栽赃,官奴脱逃本只是件小事,但他埋伏在相府的耳目却回报,敬祥对一个脱逃的官奴异常执着,不断派人暗中搜捕,引得他来了兴趣,一经调查,发现那逃奴居然自称是朱友珪生父,不管是真是假,只要这事儿一爆发,朱友珪觊觎皇位的野心必然大受打击,他哪会放过这大好良机?
敬祥不理会杨厚,直接禀报梁帝:‘陛下,臣从一奴隶逼供得知,此人对二殿下执法不阿,心有怨恨,臣又得知马郡主将此人带回渤王府,情急之下,立即赶去捉人,而臣也的确在其靴履内搜出一匕首。’他一抬手,一旁太监将一把匕首呈了上来。
摘星见到那匕首,只觉可笑!当初林广入府前,莫霄就已经搜遍他全身,若他的靴履中藏有匕首,莫霄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她想开口替林广辩解,朱友文忽扯住她的手腕,她不解地望向他,这次他依旧坚定摇头,示意她不要出声。
林广这人明显大有文章,但此刻状况不明,人又已死,任意提出证据,怕只会惹祸上身,不如静观其变。
敬祥又道:‘且此犯自尽前,已画押认罪。’
一名太监呈上林广的画押,梁帝拿起,仍感疑惑:‘当真如此?不过一名逃奴,竟胆敢冒死刺杀皇子?’
‘陛下,确实如此,臣万万不敢欺瞒!’敬祥一脸恳切。
朱友珪也道:‘父皇,儿臣数年前,奉命前去彻查军营集体藏粮一事,曾将一批涉案士兵罚降为奴,此人当时的确被贬为奴,军部皆有档备查。’
杨厚却不以为然,身为丞相,在军部文件上动动手脚,又有何难?
梁帝思量一会儿,点点头,道:‘杨校尉当初向朕禀报时,朕也觉奇怪,区区一逃奴,何以竟需堂堂丞相劳师动众?原来竟是这番缘由,老丞相可真是爱婿如子啊。’最后这句话,似意有所指,杨厚偷觑梁帝,只见他面容和蔼,并无异状。
敬祥与朱友珪同时如释重担,看来是成功瞒过梁帝了。
梁帝放下画押,语气一沈,转头看向马摘星,道:‘马郡主,妳识人不明,引狼入室,渤王府警戒疏漏,纵容逃犯,险些酿成大错,你们两人可知罪?’
‘是儿臣失察,请父皇降罪!’朱友文立即将责任一肩揽下。
‘陛下!’摘星往前站了一步,‘此事与三殿下无关!三殿下曾多次力阻,是摘星一意孤行,不听劝阻,才铸此大错,肯请陛下,仅降罪于摘星一人!’
说不恐惧,是骗人的,但在见到朱友文毫不犹豫便替她扛下这一切时,她忽然又有了勇气。人能有勇气,是因为有了依靠。但她不想连累朱友文,况且这一切的确都是她的错。
梁帝冷哼一声,先看着朱友文,‘事出渤王府,你难卸其责,朕罚你思过三月,供缴一年俸禄。’又对摘星道:‘妳受人蒙蔽,又顽固不听劝阻,置朕二子性命于危险之中,险酿大错!朕罚妳跪于太庙省思,三天三夜!’
朱友文似还想说些什么,摘星已双膝一跪,坦然接受责罚。
*
太阳逐渐西下,一日将尽,跪在太庙内的摘星虽想硬撑,但曾被马俊打断的双腿旧伤早已不堪负荷,痛得她冷汗涔涔,不但是腿,连身子也开始发抖,照这样下去,别说三天三夜,怕是连三个时辰都支持不住。
一个人影在太庙外一闪,负责看守的禁军大喝一声:‘来者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