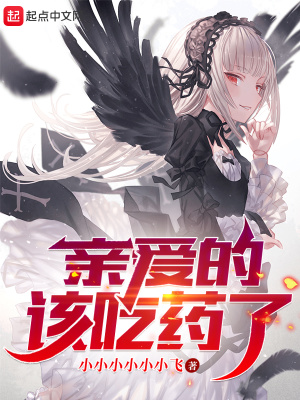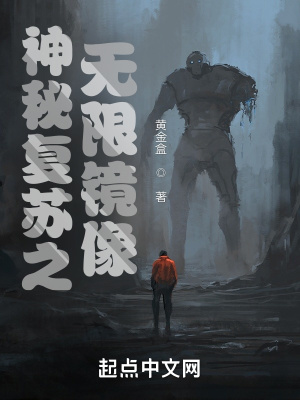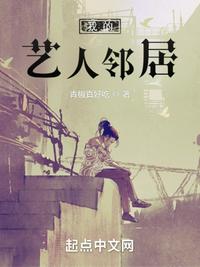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凤谋金台牛人全文阅读最新章节 > 130140(第17页)
130140(第17页)
她第一次真正打量李起年,是在拜堂后的夜晚。
那夜屋中点了两盏灯,窗纸投下他的影子。沈溪龄揭开红盖头,看见他站在不远处的灯下,白衣黑发,腰背挺直,却不近不远地与她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沈氏。”他唤她的名字时,声音极轻。
她未言,只轻轻福了一礼。他又道:“委屈你了。”
她摇头。那时她心中并无波澜,只觉得这是一段命运安排的结契,谁也不欠谁,谁也无力改变。
可自那之后,沈溪龄渐渐发现,她的这位夫君,并非传言中那般神秘不可测。
他起居极有规律,早起习文,傍晚练剑,从不懈怠。他说话简练,语气平稳,很少有怒色,却能一语中的。他身边的下人对他都颇为敬畏,不因他年轻便轻慢他,反倒是小心翼翼中透着服从。
他待她,也是不温不火。
唯有面对长史的时候,李起年才像个同龄人,嬉笑怒骂言语间全是文章。
沈溪龄从未奢求过两情相悦,她是尊敬徐圭言的,但是被排除在外的滋味不好受,她的心总是一沉一沉。
她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被人遗忘、被权力剥夺、只在熟人面前展露真面目的李起年。
圣旨传来,说要他们启程回京赴宴时,李起年脸上只淡淡应了一句“领旨谢恩”,可沈溪龄却在夜里站在屋檐下,看着雨滴敲打窗棂,一夜未眠。
她想去,想去看看繁华的长安。
但她更放不下父亲。
稀奇的,李起年对于回京的态度也很微妙,与她想象中的差距甚大。
那天夜里,她走进他的书房,看见他披着外袍坐在书案后,桌上摊着写了一半的折子。
“你不愿回京吗?”她忽然问。
李起年一愣,抬眸看她,眼中是她熟悉的温和,却也掩不住深处一丝躲闪。
他没有回答,只说:“父皇的命令。”
遇刺一事后,李起年对她有了不一样的态度。
“沈姐姐,你觉得我真的能成为太子吗?”
“你觉得,如果我这次回京,没能入得了父皇的眼,回到岭南……还会有人尊重我吗?”
她总是平静地回答,不慌不忙,可她看到李起年眼中的落寞时,心忽然揪了一下。
岭南到长安这一路,他开始找她说些琐碎的事,谈今日吃食寡淡,亦或者是梦里见到旧人;她依旧不言,只静静听。
他偶尔倚在车壁上,一边说话一边看她,她却总低着头装作专心抄文。
渐渐地,他们之间有了一些别人看不出来的默契。
好在徐长史的伤在回到长安前就好多了,没人发现她身上的伤。
归日,车马入了长安城,天色尚早,街道两侧早已戒严清道。
大批宫卫与冯家亲兵候在道旁,声势浩大。马蹄声、辘辘车声与兵刃的碰撞声混合在一起,像一张无形的网,拢住了回城者的心。
车帘半卷,徐圭言坐在内里,身姿挺拔,神色平静。
她的目光透过帘角落在车外的冯竹晋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