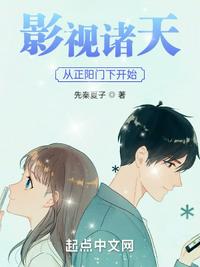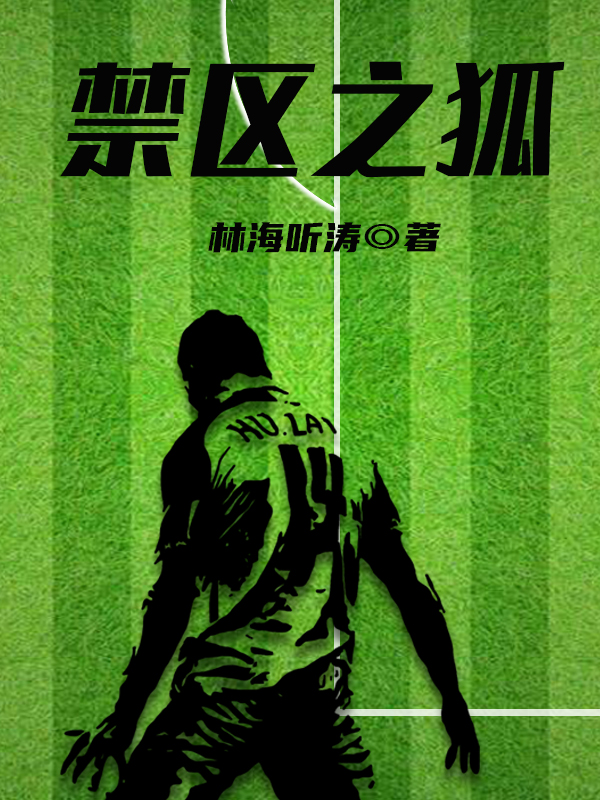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凤谋锦绣结局是悲吗 > 120130(第12页)
120130(第12页)
午后,雨水落在笑林县县衙后院的茶亭外围,光影在竹帘上摇晃,热气蒸腾的茶水氤氲开来,一碟腌渍得极咸的橄榄静静摆在桌角,空气里混着海风与草木香。
徐圭言换了便服,头发只是随意绾了个髻,坐在一侧木凳上,手中端着茶盏,目光时不时扫向前方那位年逾五旬、身形干瘦却气定神闲的县令——魏叔佑。
“魏县令,”她轻声开口,语调却不见半分寒暄客套,“朝廷这次派了不少人来,还有两日便到了,明面上说的是查水患,可我总觉得……终归不止赈灾。”
魏叔佑眼皮抬了一下,似笑非笑地看她一眼:“长史此言何意?”
徐圭言轻叹了口气,将茶盏轻轻搁在木案上,“五年了,岭南道虽不说年年风调雨顺,但也自给自足。如今陛下忽然下旨派三部官员齐至,谁信他们单是来看灾情的?依我看,这些人啊,不是看鱼塘的水深不深,另有企图吧。”
她语气虽轻,眉心却微蹙,指尖微微敲着案角。
“魏县令,”她抬眸望向他,语气一转,“……账上的银子够不够?赈灾一事必然会牵扯出账目,若真有人要查账……您这边,有没有应对的法子?”
魏叔佑没有立刻回答,只是从容地端起茶,吹了吹浮在上头的茶叶,啜了一口,才慢条斯理地说:“长史既问了,那老朽便说几句乡下事,若不入耳,还请莫怪。”
徐圭言点点头,身子微微前倾:“请讲。”
“在县衙东边有一片空地,靠着港湾,是渔民晒鱼之所。”魏叔佑说着,手指在桌上点了点,“你也知,咱们这里靠水吃水,百姓活计多依赖打渔。但为了保护鱼群繁殖,从前朝起就有个律法——每艘渔船每日捕捞不得超过多少斤,那是贞观年间定的数。”
徐圭言听到“贞观”二字,眉头微动:“那时候国库丰盈,百姓安居乐业,海中鱼群密布……今非昔比。”
“正是如此。”魏叔佑眼里浮出一丝笑意,“如今海况早不比当年,风浪多了,鱼少了,渔民单靠律法允许的那点捕捞量,莫说养家糊口,连填饱肚子都难。你说他们该怎么办?”
“自然是多捕一点。”
“对喽。”魏叔佑拍拍膝盖,像是在夸一个聪明学生,“可问题是,一旦超额捕捞,便属违法。那是要论罪的。可你若真一板一眼按律法来抓,那整个笑林县怕要闹翻天。于是呢?我们这当官的,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百姓也不举报?”
“不会。因为举报一个,等于断了所有人的饭碗。这是两败俱伤的事,谁都不傻。”
徐圭言点点头,这道理他明白,今天你举报我,明天我举报你,各家各户的鱼吃不上,最后还落得一个两败俱伤的后果。
不过她觉得,这事儿L应该是发生过很多次,最后才形成的渔民之间的一种平衡。
他顿了顿,继续道:“不过事无绝对。到了年底结账,县府银子总得有着落,于是就从这些’违规’的地方找个法子——我们派人突查几回,‘查出’一些人超额捕捞,征收点罚银;另外,还有一些鱼是没人认领的,多数是怕受罚丢下的,也有是渔船互斗后遗弃的,这些鱼便归了县衙,晒干之后再流入坊市,也是一笔银子。”
“律法这么用的吗?”
魏叔佑轻蔑一笑,“律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统治百姓的,代表着我们朝廷的态度。是你生活在一个地方的规则,不是用来保护他们的,公平公正?要是真的公平公正,每一条律法都应该由百姓的投票通过才行。但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人,能有什么资格投票,他们懂法吗?”
徐圭言听得沉默了好一会儿L,指尖转着茶盏,不由感叹:“我在岭南道五年,这些事……竟从未听闻。”
“长史身在王府,管的是封君政务,怎会留意这等小地儿L的民间勾当。”魏叔佑微笑,“这不过是地方小吏的下三路生计,原也不值得上呈。更何况,您是晋王府的长史,亲政多年,位高权重。我们这些人自不敢在您跟前说这些,只怕脏了您的眼。”
这浮,却又无法反驳。
徐圭言没有立刻作声,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像是将这一切收进心底,心觉。
良久,她低声说道:“如今若查账,恐怕天。”
魏叔佑呵呵一笑,眉毛一挑味才行。朝廷的官,穿得干净,吃得精细,鱼刺的,可不多。”
徐圭言望着远处海天交接的地方,潮风卷来海腥味,隐隐还有渔民的吆喝声,心头却逐渐沉了下来。
她忽然意识到,这岭南道,看似由她一手打理,实则在地方上依旧盘根错节、暗流涌动。而朝廷派人来,真真未必只为这场水灾,朝廷的消息她是听得不准,但总觉得有事要发生。
“魏大人,”她收敛起方才的笑意,语气低沉下来,“您这法子……虽好,但终究是临时草船借箭之术。若是上头真要动手,恐怕谁也保不了你。”
魏叔佑听罢,不恼不怒,反而一笑:“这年头,谁不是借着风头讨日子。长史,您说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