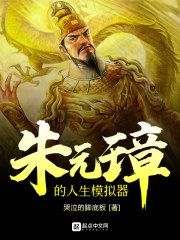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改造地府计划 > 第27章(第2页)
第27章(第2页)
“是的。”
研究生小心作答,心里有些打鼓。因为先前的几次通信,这位不知来历的刘先生得到了一定的信任,也被院内看作是半个“业内人”;也正因为是半个业内人,所以对方在《尚书》上的见解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被迅速送到研究院里罕见的几个《尚书》专家的手里——没错,即使在历史圈学术的顶峰,能够精研《尚书》,妙解无碍的大佬,仍然是少数的少数。
正因为是少数的少数,所以研究生亲自送来这样的书信,心中其实也微有忐忑,害怕信中的内容过于浅薄荒谬,招致大佬的不快。
不过,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尚书》巨擘,张教授却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冷。他抽出信纸仔细翻阅,眉毛却渐渐扬了起来,神色微有诧异。
“……相当——相当深厚的基本功。”
他轻轻道:“对尚书的内容把握得也很准确,肯定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可是,可是这信上的观点,怎么这么陈旧呢……”
他仰头思索了片刻,将书信放在了桌上:
“你先回去吧,我再好好看看。”
张教授将信纸摊在桌面上,一张一张的仔细翻阅。
越翻越他越能确定,自己刚才的判断绝无问题。这封信的确在尚书上下过苦功,无论经义还是训诂上都极为精到,是上得了台面的杰作;但一方面讲,这玩意儿的观点也太陈旧了——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其中有关于《尚书》天象预测的种种论调,似乎应该更接近于汉朝的儒家?
就算标新立异搞复古,顶多复古到唐宋也就是了,怎么还一杆子插到两千年前呢?
当然,经术研究与自然科学还是有些差异的。要是在理工科中重复两千年前的观点,那就只配和幼儿园坐一桌;但在尚书之类的冷僻古籍研究领域,无论观点多么老旧,这封信在训诂和考据上的功力,都已经足够吊打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物;甚而言之,信中在古籍释读上展示出的极高水平。就是张教授自己也是大为叹服,乃至自愧不如的。力不如人,亦不能不退一步地,承认对方的优势
……不过嘛,这个世界上研究尚书的办法,也不是只有博览古籍这一条路的。
张教授扶了一扶眼镜,镜片中闪过了微光。
作为研究院尚书研究领域的顶级大佬,张教授之所以能威震四方,所向披靡,学界人人噤声,不是因为他广览群书、博闻多知,文献功力深厚无匹(事实上,在基础功上比他厚实的人绝不是没有);而是因为他别出心裁,敢为人先,在考古中运用了某些全新的技术,拿到了意料不到的成果。
譬如说,几年前他就力主引进物理学院的精密微距识别技术,在扫描了某座战国墓地中被泡得稀烂的竹简废料之后,居然从中识别出了全本的《尚书》。
这叫什么?这就叫降维打击、这就叫一力降十会,这就叫乱拳打死老师傅——博学鸿儒和顶级专家们对着传世的残缺本《尚书》皓首穷经,可能花上几百年才能勉强猜出一个字的释义;而现在——现在,人家直接把全本《尚书》端了上来,大儒们还能多说什么?
所以,在这套竹简识别结束以后,主持项目的张教授就自动升咖了。张教授——学养未必最丰足、基础未必最牢靠、资历未必最深厚的张教授项目组,现在可以理直气壮的站在扫描仪上对学术圈喊话:
没有人!能比!我们!更懂!《尚书》!
可惜,时殊世异,有的逻辑也大大不同了。如果换做一千年前,复原《尚书》的功绩足够让朝廷欢迎鼓舞,中央高官扛着张教授到太庙上告祖先。但现在嘛……解读《尚书》当然还是伟大的成就,但总归过于冷僻,只有小圈子里寥寥无几的庆祝。
如此曲高和寡的冷清,当然叫人颇为寂寞。所以张教授读过这篇言辞颇为不逊的文章,第一反应都并不是冒犯与愤怒,而是某种棋逢对手的兴奋——他辛苦研究多年的学术,终于又有彼此共鸣的用武之地了!
这封信的深厚功力可以吊打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物;可是,这仅存的百分之零点一中,他张某人恰恰就能算上一个。踢到他张某人,你也算是踢到铁板了!
“——我可不喜欢在专业领域被外人戏弄。”
张教授轻声引述牛顿的原话,啪地一声拔开了钢笔笔帽——就仿佛将佩剑抽出了剑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