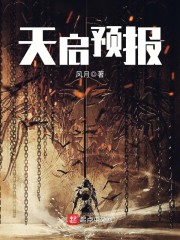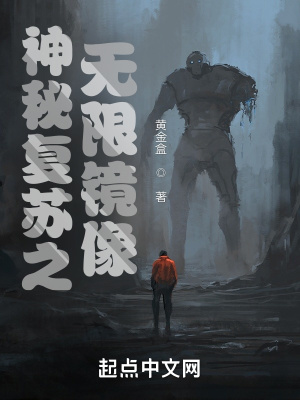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元灭金 > 第716章 盛宴(第1页)
第716章 盛宴(第1页)
虽然增加了一万精锐部队,但是海山仅以此镇压大都周边的不稳定因素。想要恢复大元朝曾经的荣光,只靠军队已经解决不了问题。
内政,必须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大量的汉人官员被提拔,乃至大肆封官授爵。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一时之间出现了许多的一二品高官。一些王公贵族,甚至连驸马都被封了“一字王”。
海山试图以此凝聚人心,却不知官爵封得越多,却会让越多的人感觉到不平衡。
有人感觉到了中兴的希望,有人则认为这是在倒行逆施,将会让大元国彻底脱离蒙古人的传统而走向灭亡。
其中反对声最大的是海山的同胞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
为了安抚自己这位摒弃了汉名“寿山”的亲弟弟,海山不仅立其为太子称“皇太弟”,还将中书省交由寿山兼领。
于是,大批蒙古老臣,包括离开怯薛军的月赤察儿与原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全都投入寿山麾下。
中书省由此几乎成为一个独立的小朝廷。
无奈之下,海山又设尚书省。以崇尚儒学的哈剌哈孙为丞相,负责新钞的发行。
作为皇帝,海山是个相当努力而且很有抱负的皇帝,但是努力的人并不一定就会成功。
如明末的崇祯。
一套组合拳下来,朝廷财政不仅没有任何的好转,反而愈加惨淡。
新钞发行半年之后,再次宣告失败。因为没有一个商人,愿意承担新钞贬值的风险而接受“至大银钞”。
蒙古官员与汉臣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大。忽必烈都未能解决的问题,对于海山而言,同样是一道根本无法逾越的鸿沟。
以寿山为首的中书省与聚集了大批汉臣的尚书省之间的矛盾,甚至超过了当年的安童与桑哥。
朝廷,在海山的努力之下,从一盘散沙变成一堆永远也聚不起来的沙末。
……
三年来,日月岛部除了彻底消化高丽所剩不多的资源与人口,进一步围困日本,大肆扩建南洋各岛国的基地,最大的收获则来自西北明军。
在商队的辅助与噶玛噶举喇嘛的配合之下,明军西出玉门关,直抵与察合台汗国相接的北庭首府别矢八里。
每下一城,明军便留下几个喇嘛,或接管城中的萨迦教派,或兴建寺庙。同时以商社的名义营建客栈、酒楼与仓库。
商业先行,寺庙相伴,军队威慑,宗教施恩。
而且明军在西域,或除暴或招收马贼,虽然不可能秋毫无犯,但轻易不涉及当地的势力之争。不过只要谁惹到了商队或是寺庙,必定千里追杀,不死不休。
由此西北明军在西域声名大振,三年时间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三万骑的雄兵。而商社也已经在天山北麓,收购了一个占地近万顷的马场,其中有天马六万匹。
至大二年秋,朝廷与江南的三年停战协议到期。只是无论是愈加糜烂的朝廷,还是高歌前行的江南,都没有哪方主动提出要延续这份协议。
江南名义上还是朝廷治下,朝廷实在无法放下脸面主动提出停战要求。
而对于江南来说,战或不战,都已经不是个问题。
若战,将朝廷势力摧毁无非是投入兵力多少、能否承受得了巨大伤亡率的问题。
不战,经济上已经无法自给自足的朝廷,终究会被温水煮熟而烂透。
但是,在寿山的主导下,中书省的声音却越发的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