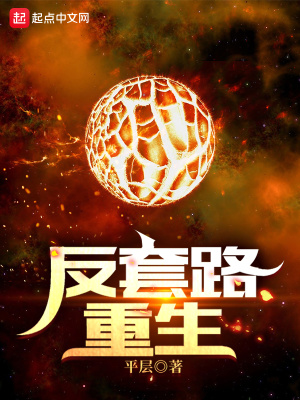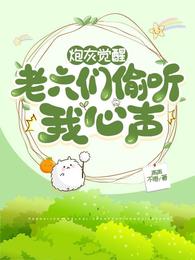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1627崛起南海全文免费 > 第3874章(第2页)
第3874章(第2页)
三司衙门此时也是左右为难,辖区内的驻军兵力本就有限,抵抗海汉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的攻势已十分吃力,而朝廷答应的外省援军却迟迟未见踪影,还在近日连下数道圣旨,要求江西死守待援。
至于所有人翘首期盼的停战谈判,如今更是连半点消息都没有。据说杭州的使馆因为主官病倒而停摆,接任的官员还在京师赶往杭州的路上,能否与海汉执委会开启谈判也仍是未知数。
舆论场上充斥着各种不利消息,从官场到民间,对于这一轮交战的前景都是十分悲观。
但形势再怎么不利,身为朝廷命官,各地官员也不能擅离职守,只能祈祷自己的辖区不会被卷入战火。
不过民间不会受此限制,选择逃离才是明智之举。所以接近战线的各处地区都开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难民潮,其中自然也不乏地方上颇有影响力的士绅人物。
但与几年前那次大规模战事有所不同的是,逃难民众所选择的方向有了显着变化,并不全是逃往大明后方腹地躲避战乱,有相当多的人却选择了逃向海汉的控制区。
原因无他,大明与海汉如今孰强孰弱,正常人大多能够分辨清楚,大明被逐渐蚕食的趋势难以逆转,即便逃往后方暂享安宁,日后也有可能还是会被下一轮的战火波及。
特别是那些原本就是早年间从江西周边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地逃难过来的民众,对于这样的趋势更是有着切身的感受。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一逃再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今真正安全的地方并不是大明的腹地,而是在敌国的控制区。
当然了,等自己逃过去之后,敌国就不再是敌国了。前期逃往海汉的人,可有不少已经过上了好日子,这也并不是什么秘密。
而社会上层人物因为能够接触到的信息更多,所以对此的认识也更为清楚,也更乐意逃往海汉躲避战乱。
特别是江西北部地区,借助长江航运通道与海汉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对于海汉的情况比较清楚,而且九江府在战前就已经有大批富商权贵偷偷跑到了海汉所辖的南京等地,如今有些人甚至已经通过置产投资在海汉入籍了。
江西这边就算仗打得再怎么惨烈,对这些已经逃到海汉的人来说也已经无关痛痒了。虽然留在江西带不走的不动产或许会遭受一些损失,但至少不用再担心人身安全了。
而江西南部与广东、福建接壤的地区,大多是位于连绵不断的岭南山区,交通不便,环境自然也比较闭塞,与海汉的交往相对较少,敌意比较深重,逃往海汉的人比起北边就要少一些。
这也是为何赣州明明有知府项淳夫这个内应,却依然出现了多起抵抗事件,大大延缓了海汉占领赣州的进程。
五月一日,石成武所率的武装舰队沿鄱阳湖水道南下,抵达了南康府城所在地。守军几乎没有在水面上做出任何抵抗,便让出了湖岸,龟缩至城内死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