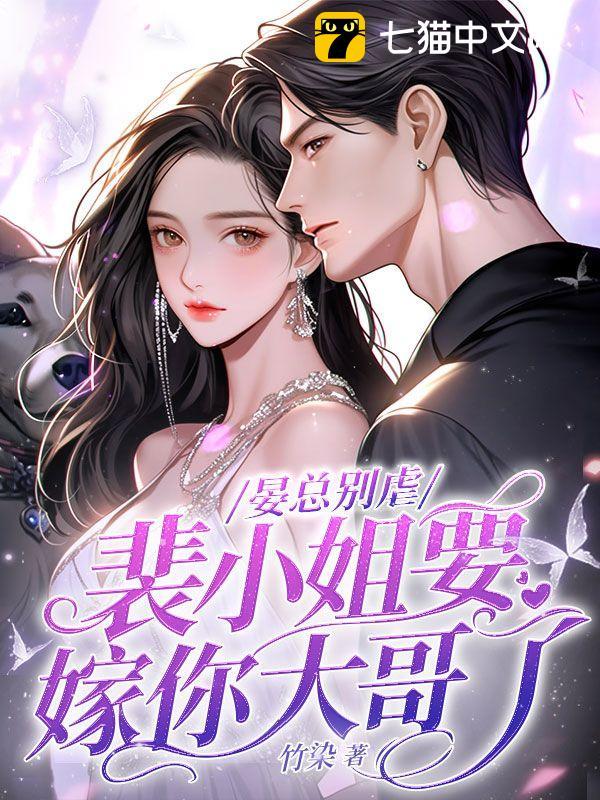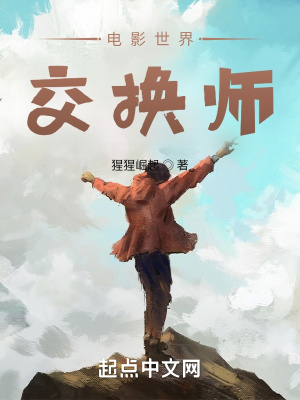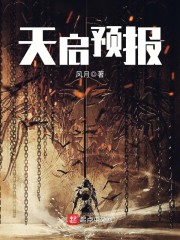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簪笔集讲的什么 > 8090(第33页)
8090(第33页)
故而从她笔下流淌出的,岂是寻常闺阁闲情?
由她来执笔,无论是续写正史,还是撰写话本,字字句句都将带着千古红颜的喜乐悲辛。
所以孔珂询问了祝昭:“若你是史官,会如何记录历史。”
祝昭答:“寸楮尺字,孜孜以求。”
孔珂很满意她的回答。
孔珂心里清楚,为女子修史立传,于当今朝堂,断难跻身正史之列。然则,正史阙如,何妨另辟蹊径?
正史不容,话本可载。
借传奇之笔,铺陈悲欢,摹写群钗,使其事迹风骨得以流传于闾巷,播扬于后世。此时此刻,女子之名、女子之事,能载于方册,不令湮灭,已是亘古未有的大进步。
那日在藏书阁,孔珂望着祝昭远去的背影,转身朝着徽州的方向遥遥一拜:“先生,请原谅我的私心。”
让祝昭为女子写史立传是她从那日开始就有的布局,她机关算尽,拉上了自己的女儿。
她真的收到了平康从瑕州传来的书信,信中交代了平康自己的现状,和祝昭决意以簪为笔为女子写史的决心。
那一刻,她笑容温和地向着瑕州的方向望去。
那一刻,远在瑕州的祝昭朝着元安叩首之时,好似隔着万千山水和久远的时间又和孔珂见了一面,这一面中,她温和一笑。
只不过这些关于想让祝昭著史的私心孔珂都埋藏于心,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她的女儿萧朔华,她只对萧朔华说,她的私心是希望祝昭能成为祝昭。
陛下寿宴第二日孔珂才惊闻昨夜平康公主诣阙,为求祝昭入公主府而触忤天颜,竟遭批颊。
她心下忧急如焚,立刻遣中使驰赴公主府邸,宣召入宫,使者却返报殿下去了九松寺。
孔珂深知自己女儿的心性,生于天家锦绣,自养就一身矜贵傲骨。
但是平康的傲气,半是睥睨须眉,半是恪守金枝之责。
孔珂追根究底地反思过,萧朔华成为了如今的平康,她孔珂难辞其咎。
平康髫龄稚幼时,孔珂常同她絮絮,吐胸中块垒不平之语,日积月累,致使她忧思之深,犹胜自己。
在孔珂无形的影响下,萧朔华会常常自感肩承千钧,负大雍万姓蛾眉的命运,夙夜匪懈,思之行之,未尝稍息。
孔珂扪心自问,难道她不乐见一国的公主殿下有此襟抱?
她乐见的。
但是慈母衷肠,实不忍所有风霜,只得萧朔华一肩独担。
萧朔华常常和她这个忧思的母亲说,她如今已经不单单是萧朔华了,她更是平康公主,是大雍的平康公主。
而在萧朔华眼中,孔珂是倦看六宫纷争之人,她曾经听闻母后喟叹:“入此宫闱者,皆似飞鸟入樊笼。既陷囹圄,纵使相搏,终是两败俱伤,何如静思同坐,共问一句:你我缘何皆在此笼中?笼外或有豺虎眈眈,笼内却属同命相连。同类相煎,岂非至悲?”
正因中宫仁厚若此,更兼思虑深湛,六宫妃嫔竟也和睦相亲,颇存温情。
萧朔华幼时,萧桓还是皇子,尝于诸位侧妃衣香鬓影间,得沐慈晖,承惠良多,相较君父天威,她反觉与诸位妃子更见亲昵。
是以她心念笃定,身受此恩,当如涓流汇海,泽被苍生,方不负所承之情。
今上膝下三子二女。
嫡长子为太子萧竟,嫡长女封平康公主萧朔华,皆中宫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