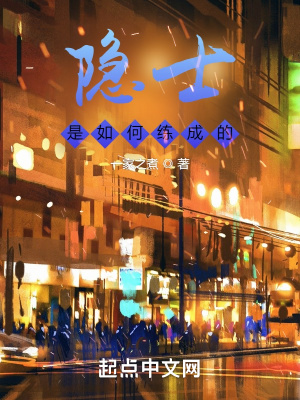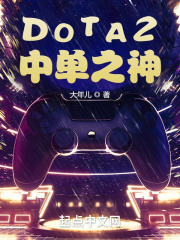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她在红棉厂六零晋江 > 3第 3 章(第1页)
3第 3 章(第1页)
黎棠第一次拉板车一开始不知道怎么使力,跑起来歪歪扭扭的,拉了一段距离才慢慢会用点巧劲了。
冯老太太是缠过足的小脚,本来就走不快,一路小跑在后头推车,咬着蛮一口气都没歇。婆孙俩一前一后绕过西织车间那一溜厂房,便到了红棉厂的后巷。
那间土坯屋在后巷最东头,红棉厂后巷在厂区最北面,挨着几个仓库,是以前红棉厂用来养猪的地方。眼下困难时期,人都吃不饱,何况猪。厂里的猪养不起来,猪棚自然废弃了。
黎棠站在门口,眯着眼睛看过去,整个人凉了半截——这是她们接下来要落脚的地儿?
土坯屋的顶棚是芦苇秆做的,倾斜的草顶像蓬乱的头发一样披散下来,把门窗给挡得严严实实。看上去已经荒了一段时间了。前院倒是挺大,还是块硬地,估计是以前食堂用来晒东西的。东头角落的压水井看上去锈迹斑斑,也不知道有用没用。
在原来的世界,她也算是走南闯北的人了,看到土坯屋还是傻眼了,没见过条件这么差的屋子。身后冯老太太已经开始收拾东西了,老太太解放前是纺织老板的姨太太,解放后又跟着女儿女婿一起生活。
除了那几年逃难,一辈子都没吃过啥苦头。
她都不嫌弃这么差的居住环境,自己又有什么好嫌弃的呢?
这么一想,黎棠便停止了伤春悲秋,赶紧和姥姥一起把家当给卸下来。得趁着天黑前把板车给人送回去。婆孙俩把车上的物品一样样搬到门口的空地上,等全部搬完太阳已经下山了。
冯老太太拍了拍棉袄上的灰:“我去把板车还了。刘师傅明天一早还要搬菜。”
黎棠顿了顿,放下手里的活:“是食堂那个刘师傅吧?他家我知道在哪,我去还吧。”
冯翠贞:“我去就行了。你先把床铺好,其他东西放那,明天再整理。”
姥姥坚持,黎棠便没再说什么,留下来整理东西,将门口的物品一样样往屋里搬。
推开门,霉味夹杂着动物粪便的气息直往鼻腔里蹿,虽然这地方早就不养猪了,那股气味却并没有散去。
屋里只有一张用土坯砌的床,床铺上铺了一些稻草,很明显老太太已经提前过来整理了。黎棠在稻草上面铺了层棉花胎,再铺上床单,剩下的那床棉被便当作盖被了。在大杂院婆孙俩也是睡一床,这张土坯床比那木板床还要宽敞些。
整理完床铺,屋里已经黑透了,黎棠赶紧拿出煤油灯点上,将煤炉子拎到外面开始烧水。引火的纸,得用报纸,因为报纸上有油墨,容易烧,然后再点着那个细的木条,再放上几块大的劈柴,等劈柴烧着了,劈柴上面的煤球就容易点着了。
炉腔里很快蹿出来的火苗,黎棠将钢精锅放在炉子上,加满水。水烧开了,兑在热水瓶里,然后开始煮棒碴粥。分家就分到这么一口钢精锅,以后烧水、煮饭、做菜都得靠它。
看着翻滚的棒碴粥,黎棠有些愣神。
刚才一个接一个的活干下来,她完全没动脑子,全凭身体留下来的惯性在干着。
原主只是不想当纺织工人,过日子的技能并不缺。
冯翠贞回来的时候,看到棠丫头把热粥热水端上了桌,就连李婶给的窝头都热好了,感觉被风吹得冷透的身子都暖了起来。
婆孙俩坐下来吃饭,今天干了不少体力活,这会早饿得前胸贴后背。
冯翠贞看着碗里两个窝头,夹了一个到外孙女碗里:“明天早上不用给我热窝头了,我喝粥就行了。”
黎棠知道姥姥在担心什么,粮袋里根本没多少粮,这几个窝头还是临走前李婶塞进他们褥子里的。这次分家,冯翠贞已经把婆孙俩的户口本和粮油关系从女婿那迁出来了。
黎棠在车间当扫地工,每个月粮食三十斤,冯翠贞一个月也能从街道领二十七斤粮食。分家后,婆孙俩粮食倒不缺,其它就紧巴巴的了。毕竟在车间当扫地工,一个月工资才十四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