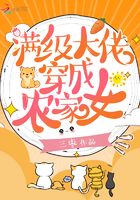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红衣半狼藉山负雪 > 23朝不回一修(第3页)
23朝不回一修(第3页)
殷素抬目朝王代玉告谢,“劳婶母费心,我用着甚好,明儿也要再支着试试。”
王代玉喜色更甚,连连道好,又自堂前坐下,端起云裁方斟好的热茶。
“今儿个你叔父出宅,遇上位旧友,相谈甚欢,要替他在上元城谋份清闲差事呢。便是在尊经阁里校对古籍,守守阁楼万书,这既合了你叔父不愿入仕的心,又能叫家中有几分薄资。”
殷素陡闻一愣,连着沈却亦是一惊。
“父亲身困大梁之时,便驳了入开封府的请令,后颍州刺史亲请父亲做州学博士,亦婉拒,如何竟会应下杨吴上元差事?”
“你阿耶看重杨吴,不喜大梁与晋,你又不是不知晓。”王代玉搁了茶盏,撇嘴言:“若非咱们老根生在颍州,大梁与晋国又闹得厉害,你阿耶恐一辈子不再沾官,要在颍州一直耗着呢。”
“现下他肯有这个心思,乃是好事。”王代玉望向沈却,目中攀上些愁絮,“不然,你阿耶也要拘着你一辈子。”
“遇之,既然他肯松了杨吴这道口,你不妨也试试,去做想行之事。”
她知晓亲子心绪,也痛心丈夫旧疾,可如今一家子脱了苦海,落脚处安稳,便也该朝前望。
幼时几卷圣贤书烂熟于心,听着他父亲鸿鹄壮志而长,又有哪位少年人,肯隐隐于世,做位槛外人。
“杨吴民风淳朴,上与大梁淮水相隔,下处旁国又不敌他强劲富庶,倒为稳富之地,况校对古籍难卷入些虎穴狼窝,乃是个清净差位。”
殷素虽慢慢出声,心却还落于沈却与王夫人相对的前话。
她忆起些旧事。
与沈却还未相识之前,阿耶阿娘口中常提及的,是沈顷与王代玉。
阿耶说文官可怜,顶着旧唐高官名号的文官更是可怜。
沈宅一家,便是那个可怜人。
唐末气象残若枯枝败叶。
宰相随着惊慌失措的皇帝辗转各地,便有雄心,只余空喊悲愤。他们夹杂在中官、使君与皇帝之中,辗转难立,无论依附于谁,皆难逃厄运悲剧。
沈顷极早看清这一事实。
亦急切想要摆脱一眼可望到头的命运。
于是在阿耶的推波助澜下,这顶宰相乌纱帽被掀翻,沈顷一路自长安被贬颍州。
那时颍州战乱频频,苦日子难言于表,但沈顷甘之如饴。
比起呐喊无门,如今他身立颍州,倒还能仰天唤一声痛快。
直到唐廷不复存在,朱梁横空而起,带血利剑一击便刺穿颍州看似平静的日子。
大梁急需一个正身立命的机会,他拿着唐廷玉玺,披着皇帝袍衣,犹觉不定民心。
于是旧唐官员,成了新帝下一个目标。
沈顷一家人被明请暗逼地来到开封府。
再一次辗转皇帝跟前,拒绝并非轻而易举,沈顷身上系着一家老小的性命,他不愿再卷入漩涡,却又不敢直抒胸臆。
直至阿耶带着她自幽州而来。
沈顷见着他时,目中惊愕,久久不能回神。
或许在沈顷眼里,阿耶还是个好人,不该是随大梁一道割据的藩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