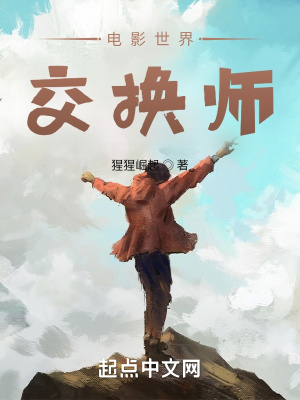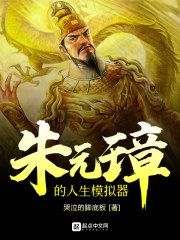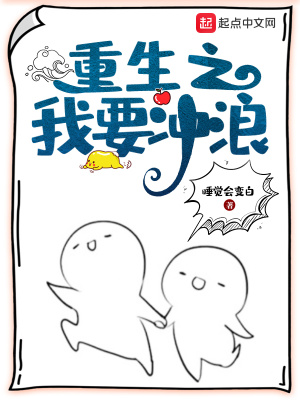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穿越1900年主宰东北 热爱摸鱼 > 第334章 经济隐忧初现 虎币下的泡沫(第1页)
第334章 经济隐忧初现 虎币下的泡沫(第1页)
1925年冬,奉天城,帝国中央银行总部。
窗外寒风凛冽,室内却温暖如春,甚至带着一丝燥热。
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无数代表虎币流动、大宗商品价格、工业产出、殖民地物资输送的光带交织穿梭,构成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帝国经济脉络图。
然而,在这幅看似繁荣鼎盛的图景中,几条刺眼的红色警报信号正在顽固地闪烁,并且有逐渐蔓延的趋势。
财政总长王永江眉头紧锁,手中的指挥杆点在几条异常波动的光带上,他的声音失去了往日的从容,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焦虑。
“首席,各位同僚。”
他深吸一口气。
“帝国的经济,正在发烧。”
他调出一组数据:
“这是过去半年的虎币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是工业产出增速的三倍以上。
大量的货币,通过全球投资计划、国内基建项目、特别是军工复合体转向民用的‘凤凰计划’,被注入经济体。”
“钱太多了。”
王永江一针见血。
“它们没有全部进入实体经济循环,而是涌入了资产领域。”
指挥杆指向几个关键节点:
“奉天、沪上、闽省等核心城市的地价,在过去一年平均上涨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一座普通的四合院,价格堪比战前的一座小型工厂!”
“帝国证券交易所的主要股指,市盈率普遍超过五十倍,甚至出现上百倍的‘概念股’,完全脱离了企业盈利能力。”
“古玩、艺术品、乃至新型的‘航空概念’投机……泡沫无处不在。
人们沉迷于‘虎币永不贬值’的神话,疯狂加杠杆追逐利润,实业精神正在被腐蚀。”
内政总长赵铭补充道,面色凝重:
“更严重的是输入性通胀。
我们强制要求殖民地以虎币结算,低价输出原料,但他们的生产能力有限,而我们的需求无穷。
这导致全球原材料价格被动推高,反过来又通过进口冲击我们的生产成本。
工厂主们抱怨利润被挤压,而工人则要求加薪以应对物价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