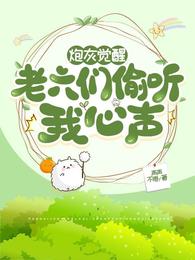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天子宁有种皇三皮 > 第二百零八章 郊祀和赏赐(第2页)
第二百零八章 郊祀和赏赐(第2页)
李奕控马前行,位置就在玉辂前方十丈之内,正好处于导驾骑卫与黄麾仪仗之间的空当。
他目光如鹰隼,锐利地扫视着整个队伍行进中的每一个细节。
宽阔的御道两旁,禁军持戈肃立,隔绝一切闲杂,形成一道刀枪林立的冰冷人墙。
队伍每前进一里,便有号令由前至后,再由后至前地传递,确保步调如一,阵列森严。
寒日艰难地爬上城头,将苍白的光投在浩荡队伍上,但暖意未至。
直到巳时将至,卤簿队伍出了南熏门,再往南郊行进数里,圜丘终于在视野尽头浮现。
圜丘祭坛,三重圆台,象征天圆之地。
坛体以汉白玉石铺砌,在冬日不甚明艳的阳光下,泛着冰冷却神圣的光泽。
当先导的骑卫抵达圜丘壝门之外时,庄严的《引祥乐》旋律便戛然而止,随之转为低沉肃穆的祭乐。
就在这凝重的氛围之下,皇帝所乘坐的玉辂车驾,停在了临时搭建的青幔帷宫前。
这座为天子祭祀斋戒而临时构筑的“行在”,虽是木竹为骨、青幔覆身,却规制俨然,设门阙旗幡,巨大的青色幔帐,在朔风中微微鼓荡。
车帘被侍御官恭敬掀起,一袭玄黑大裘冕服的皇帝,被近侍搀扶着下了马车。
世宗柴荣步履沉稳地踏进了帷宫,为接下来的祭天大礼做最后准备。
与此同时,李奕早已翻身下马,与礼部、太常寺等官吏一起,协调安排各方的站位、次序。
自五代以来,皇帝亲行祭祀、大礼时,便会临时设置使职,事讫则罢。
后唐时完善为五使,以宰相为大礼使,兵部尚书为礼仪使,御史中丞为仪仗使,兵部侍郎为卤簿使,开封尹为顿递使。
后周沿袭此制,惟以礼仪使改归太常寺,合称为“南郊五使”。
但惯例不代表就一定,特别是在乱世的背景下,某些时候全凭皇帝个人的决断。
因此,在这次郊祀,除了顿递使空置外,另以首相范质为南郊大礼使,宣徽南院使向训为礼仪使,左散骑常侍王朴为仪仗使。
同时又以李奕为“权判卤簿使”。
不过范质乃宰辅之尊,担任皇帝的陪位助祭,无须劳心操持诸多杂事。
而向训、王朴二人则挂个名头,荣誉性质大于实际作用,具体的执行还是归于有司官吏。
反倒是李奕,虽挂着“权判”之职,但却要负责协助各类事宜。
……随着指令传达下去。
导驾骑卫分列壝门左右两侧,肃立警戒。
黄麾仪仗、旗队、幡幢、刀枪仪仗、金瓜骨朵卫队等,按照严格规制,有序地鱼贯进入壝门之内,在青阶圆坛的四周列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