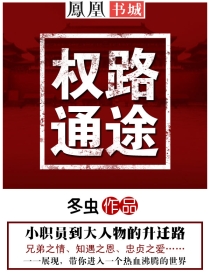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重生到香江 > 第28章 固定资产求收藏月票推荐票求追读(第3页)
第28章 固定资产求收藏月票推荐票求追读(第3页)
离开会计师事务所,陈秉文和高振海走在熙熙攘攘的中环街头。
摩天大楼林立,金融精英步履匆匆,空气中弥漫着资本的味道。
陈秉文心中激荡,他知道,陈记的舞台,将从深水埗的街头,逐渐延伸到这里。
“文哥,成立公司,注册这么多东西,感觉一下子正规了好多,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高振海感慨道。
“阿海,这只是开始。”陈秉文拍拍他肩膀,“公司是壳子,里面装的东西要越来越值钱,才是本事。
新品研发和瓶装化项目,就是往里装的金子。”
想到方文山对固定资产重要性的强调,陈秉文清楚,买下厂房是夯实根基的第一步。
他迅速锁定了最易突破的目标,长沙湾食品厂的原老板钟伯。
这位房东因儿子移民加拿大急于出手,上次押一付一的短租协议就透露出他的套现需求。
现在正是彻底拿下的最佳时机。
陈秉文没有耽搁,当天下午就在深水埗一间安静的茶楼包间,再次与钟伯会面。
比起上次的焦急,钟伯此刻气定神闲了许多,显然移民事宜已步入正轨。
“钟伯,恭喜您即将与家人团聚。”陈秉文笑容真诚祝贺道:“上次承蒙关照,短租解我燃眉之急。
这次冒昧请您出来,是想谈谈。。。。。。永久解决这间厂的问题。”
钟伯呷了口茶,不动声色:“哦?阿文你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想长租?
可以谈,不过现在市道好,租金。。。。。。”
“不,钟伯,”陈秉文打断他,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我想买。
连同厂里的设备,打包买下来。”
钟伯端着茶杯的手顿住了,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买?
阿文,这间厂地段虽然不算顶尖,但胜在实用,面积也够。
去年行情不好,我开价年租三万是急用钱。
现在嘛。。。。。。”他拖长了语调,“厂房加设备,一口价,三十五万。”
三十五万!陈秉文心中冷笑。
这价格远超实际价值,几乎是按黄金地段新建厂房的溢价来喊。
设备是二手且已使用多年,估值极低。
钟伯显然吃准了他急需稳定的生产场所。
陈秉文没有立刻还价,而是拿出了一份文件推过去。“钟伯,这是我在观塘新厂隔壁那个仓库的五年长租约,刚签的,年租三万五,押三付一。”
他指着租约上清晰的条款和金额。“我本打算把长沙湾厂的生产逐步迁过去整合,那边空间更大,物流也更便利。
买下您这里,更多是出于一份情谊和对稳定性的考虑,毕竟工人熟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