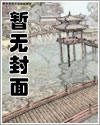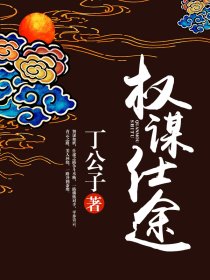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有哪些美强惨的角色 > 3040(第12页)
3040(第12页)
姜辞展平信纸,落座案前,执笔凝思良久,方才在墨砚中轻轻点蘸,提笔写下首句:
“父亲大人亲启。”
字迹工整秀雅,一如她素日性情。
她略一思索,随即执笔疾书,将宁陵之事一一落下:
“女儿随夫君入宁陵境,沿途水患所及,田庐尽毁,百姓多有流离之苦。宁陵城中原有户籍之人尚且不足,此番又涌入数百外乡灾民,现今城东一隅,堆卧者数名,皆席地而眠。郡守言及仓中储粮本就不丰,又因前月已拨数批赈粮,余粮所剩无几,恐支撑不过旬日。药材亦告匮乏,疫病之虞,不可不虑。”
她写得稳重,不言情绪,不加渲染,唯有一字一句,如实陈情,沉静却自带分量。
随即,又写道:
“请父亲设法于凉州调拨谷米三千石,草药若干,若能再遣信使带些人手前来,则不胜感激。”
写至此处,她略一顿笔,笔锋微沉。
屋外风声扫过竹影,她忽而忆起今晨路上所见的一双童眼,黯而无光,分明未及七八岁,却早已习得颠沛流离之态。她眼中轻轻一酸,又迅速定神,将杂念拂去。
最后,她收笔,缓缓落下:
“女儿近来一切安好,膳食起居俱平,身边亦有晚娘与银霜相伴,婆母相护然彼此相敬有加,与夫君行止之间,亦多照拂,无甚不谐。父亲大人若念我处境,还请宽心,烦父亲勿念。此信事关赈济,望父亲见信后勿怠,能早一日筹措,便早一日安稳。”
末尾题款:“女姜辞叩呈。”
这不是她第一次为百姓求援,但却是第一次,在他身边为他的百姓求援。如今她不知自己能为姬阳分担几何,只愿这一封信,能替宁陵争得些许喘息之机。
封好信,她将信递给守在旁边的银霜,语气认真:“这封信交给你,宁陵与凉州就一河之隔,你找人快马加鞭送去凉州,就说紧急,让他尽他所能,最好能派些人手来。”
银霜接过信郑重点头:“奴婢明白。”
姜辞送走银霜,房中渐归清寂。
她坐回桌边,伸手拎起那只白瓷瓶,微一犹豫,站起身来走至铜镜前,轻解衣襟,将右肩衣物褪下,那处瘀伤已从青紫转为淡青,触之仍隐隐作痛。
她轻启瓶盖,指腹蘸药,动作细缓地一点一点抹上。
姬阳回到东阳军营,夜色已沉,营帐内灯火摇曳,光影映得几人神色沉凝。
陆临川正倚案而立,见他入内,微微颔首。帐中还有副将杜孟秋,身着甲胄,神色凝重,宁陵郡守裴承绪亦立于侧前,手中仍握着方才送来的郡中简报。
姬阳未多言,抬手解开束在腰间的竹筒,自其中抽出一幅素纸舆图。那是姜辞今晨所绘,纸面清润,墨痕未干,几处关键水渠与堤坝位置以朱笔细注,虽非专业,但也大致明了地势走势。
他将舆图摊于案上,指节敲了敲一处河堤转折之地:“这里若再遭一场暴雨,怕是整个城南就要被淹。”
杜孟秋上前一步,拱手道:“都督所言不差,小的已派人沿此地勘察,但堤体年久失修,土质松散,临时修补,怕是杯水车薪。”
裴承绪神色难安,低声说道:“眼下可调配的民力不过两百余人,且大半年老体弱,实难胜重活。”
陆临川目光在舆图上扫了一眼,沉声道:“如今只能走西岭绕路,派兵护送粮车,但地势崎岖,辎重行得缓慢。即便今夜写信回丰都请求支援,粮草最快也要十日之后方能抵达。”
“而我们……”裴承绪眉头紧锁,“最多只可支撑六日。”
帐中陷入短暂的沉默。风穿帐帘,吹得烛火微颤。
姬阳低垂着眼,指尖缓缓抚过舆图上标注的“宁陵”二字,语气低沉:“河对岸就是凉州。”
一句话落下,众人皆未作声。
陆临川看了他一眼,知他心中所忌。他不愿低头向姜怀策求援,哪怕隔着一河,唾手可得的粮草与人力,他也不愿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