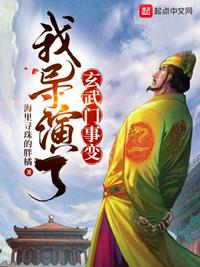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观心自在是什么意思 > 104第 104 章(第2页)
104第 104 章(第2页)
“嗯?”施也眨了眨眼,问道,“你想问什么?”
“没有啊!”郎月慈拉开距离,“你想多了。”
施也微微一笑,说:“真的?”
郎月慈败下阵来,他在施也肩头蹭了两下,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到今天才发现,大家好像还是跟你有距离。”
“这很正常。”施也腾出一只手和郎月慈十指相扣,“今天这样的工作环境,我不觉得别扭,也不觉得孤单。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
郎月慈拉着两个人相握的手放到唇边,在施也的手背上亲了一口,没说话。
施也用拇指摩挲着郎月慈的手背,温柔地问道:“在最开始,你对我的感觉是什么?或者更详细一点,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郎月慈偏头想了想,回答说:“最开始觉得你挺柔和的,但后来接触下来发现你其实是外柔内刚。有一阵我觉得你像水一样,看着很平和,但内心很有力量。后来……如果继续用比喻的话,感觉你更像树吧,可能跟你这个老师身份有关系?毕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话从小听到大了。”
“嗯。跟我对自己的判断和定位差不多。我可以并且愿意做一个提供帮助的人。渴了来喝水,热了来树荫底下乘个凉。但喝水的人不需要追溯上游水源,乘凉的人也不必知道树龄几何。这样大家都很舒服,不是吗?”施也捏着郎月慈的手,耐心解释道,“我有我自己观察这个世界的方式,同时,我也更倾向于用独处来沉淀并且丰富自我。所以,大量密集的社交会给我提供研究方向的需求,那是‘施教授’需要的;但少而精的人际结构是抛开一切社会身份的施也本人的需求。工作中的这种有距离的交往对我来说反而有益,如果我真的跟谁都能交心当朋友,那我就不够客观了。”
“所以我还是吃亏了。我有时觉得,我甚至比不上早年间你的那些‘来访者’。”郎月慈说。
施也问:“就那么想让我分析你?”
郎月慈点头。
“分析什么?”施也玩笑道,“分析你什么时候会手抖,根源是什么,带你做认知行为疗法,做暴露治疗,找准现实锚点。或者来次结构式访谈,做个pcl-5量表?”
“我没跟你开玩笑。”郎月慈撇了下嘴。
施也稍敛笑意,但语气中还是带着半开玩笑的调侃:“好吧,那我带你进行一次认知重构,分析一下,你为什么需要通过专业解构来确认自己被需求被在乎。”
“你……”连续几个专业名词已经把郎月慈绕晕了。
“还是说——”施也侧头亲了一下郎月慈的脸颊,“还是说你只是想让我告诉你,我早就把你看穿了,只是不愿意把你当病例来分析?”
郎月慈耳根微红,用沉默来应对。
施也见状终于完全收起了笑闹调侃,他的语气变得低缓,极具安抚:“那我给你一个正式的回答。你从来不是我的来访,更不是我写进论文里的案例。你是我的爱人,是我摒弃专业冲动去用心接触、呵护的人。给你做认知重构那是咨询师的工作,而我要做的,是陪你重建安全感。”
“但我还是觉得吃亏。”郎月慈嘟囔着。
施也思考片刻,说:“我给你私人定制一套提升幸福感的长期方案做补偿,行吗?”
“什么方案?”
施也满含笑意:“包括但不限于陪你运动恢复、盯着你按时吃饭、陪你聊天调节心情。还有,在你试图打破边界,用各种方式窥探我对你的分析结果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不知道。”
郎月慈的手臂用了力,把施也搂得更紧了,他的声音很轻,很小心,但又很坚定:“可以,但不够。我还想要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