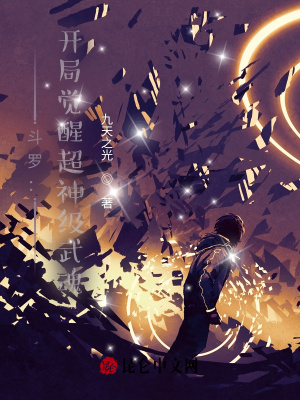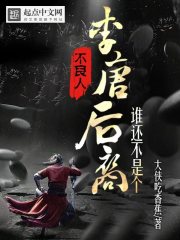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南有嘉卉 > 11孤独(第1页)
11孤独(第1页)
谢砚之没有回去,他提着书,去了离村落有段距离的茶摊下看书。
茶摊是居住在这附近的一位老学究开的,这位老学究姓陈,名叫陈弦,上了年纪,四十几岁,之前也曾通过九品中正制的方法进了朝中做了县令,因为是非势族的文臣,所以即便身有才华,也无法受到重用。
凡是九品中正,定会以衡量对方有无家学渊源,抑或是在朝中是否有得力的支柱,可惜陈弦都没有,所以他只能被定位为下品,出头的机会也少之又少。
久而久之,陈弦便也放弃了为国效力的想法,庸碌的做着朝廷的普通官员。
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许是对这世道心灰意冷,便带着妻儿离开,回到吴郡隐居。
索性祖上产业颇丰,也算是个小小的富户,所以在这里开茶摊,也只是为了写些散记。
见到谢砚之又来了茶摊,陈弦倒上一壶茶,叹了口气,给他烧茶又倒入他的碗中:“又闷闷不乐的?前些日子村里的那些孩子抢你的书,想欺负你的事,你是不是没跟他们讲?”
“你呀你。”陈弦似乎有些恨铁不成钢:“明明错不在你,为何不告诉林有为和张氏?这又不是你的错,白天受了欺负,还要做活,晚上又要去听他们的流言蜚语。”
这些事情其实与陈弦并无多少关系,他本就是到这里养老躲清静,十三岁的少年已经不算孩童,心智已近成人。
若是世族中的子弟,往往已在朝廷上领了一官半职,都正是会心机算计,想办法抱团排挤自己不喜欢的人的年纪,又怎么会是昔日里的垂髫孩童?
明哲保身的道理,世人皆知,陈弦一开始也不想过多评判,但谢砚之实在令他有些心疼。
而谢砚之只是低着头,沉默了半晌,并不答话,他手中借阅的书籍还牢牢地护在手里,今早上从集市里借了这本新书回来后,村里的几个孩子嬉笑打闹,觉得谢砚之每天只会读那些无用的圣贤书,以许家儿子许勇为首的少年把他团团围住,一哄而上,想去抢夺谢砚之手中的书。
“你把什么破书抱得这么宝贵?”许勇显然是一直瞧不上谢砚之这副做派,他还带着几个跟班的小郎君紧随其后。
平时谢砚之一直是独来独往,不和其他人亲近,主要原因是,村里没什么人喜欢读书,谢砚之除外。
那些小郎君们觉得读书也没什么用,这辈子兴许就是这样过,就算拼命地想出人头地,想得再好,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再者,谢砚之总是一副洞悉世事,通达明理的做派,也很是让他们不满。
他在村子里是不受欢迎的存在,几乎人人都知道谢砚之是林家捡回来的没爹没娘的野孩子,就算可能是富贵人家遗留下来的遗孤,但这么些年,也从未见过有人来寻。
结合谢砚之的身世,还有他爱读书的习惯,孩子们先入为主地会认为谢砚之是假清高,随了他早亡的父亲的爱读书的性子,在不爱读书的少年里,谢砚之这样是异类,也是不会被宽容的存在,况且偏远乡下的小女娘们都一心因为他的好样貌而爱慕于他,更会引起一众小郎君们的妒忌。
那些小郎君们自发地排外,孩童们的恶意有时过于明显。
于是就出现了早上的那一幕。
许勇指示跟班们去抢谢砚之怀里的书,但他就算被按在地上也不肯撒手。
几个蛮力做农活的少年去按着谢砚之,他还要护住怀中的书,双拳难敌四手,他被人按在地上抢夺,身上都抓出了红痕,却还是一声未吭,若不是陈弦撞见,制止住了他们,恐怕谢砚之身上还要受更多的伤。
他的衣服都被人抓破,却还是将书好好保存起来。
谢砚之方才回家的时候,小臂上也有红痕,却将其掩盖在衣服下,是不愿让林家人看到,却在进门时听到了那样的话。
谢砚之没说什么,也不愿让林有为看到自己这副模样。
他有些闷闷地想着,或许他的存在的确是众人眼中的异类,或许他再怎么样努力读书,都不可能有商鞅那样的际遇,时势造英雄,而当今的朝廷不是会选贤举能的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