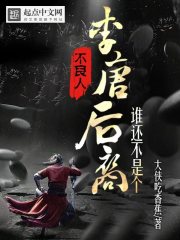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我为大明续运三百年动漫 > 第2303章 坐等朝廷打脸反被朝廷打脸(第2页)
第2303章 坐等朝廷打脸反被朝廷打脸(第2页)
你知道大旱的程度不会日益严重?
你知道国库里还有多少粮食可供赈灾的?
会不会出现蝗灾、地震等其他的灾难?
上面的五个问题无论是哪一个出现了问题,那么大概率就会是饿殍遍野,遍地哀嚎。
更何况大旱之后必有大涝,大涝之后必有大疫,也就是说现如今的大旱即便能平稳的渡过去,那么还有水灾、瘟疫两重灾难在等着他们。
水灾能往高处躲一躲,可房子大概率会冲毁掉,建房要不要银子?朝廷即便是会有一些补偿,但也不可能全部承担,自己依旧要承担大部分。
这就是雪上加霜。
水火无情,还能有逃避的空间,可瘟疫呢?
这玩意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会因为你是皇亲国戚、天子贵胄、贫穷百姓就不感染你。
一旦感染死亡风险低则两成,高则五六成。
会不会从大明境内传到新疆不好说,但地广人稀之下,感染的几率小很多。
抛开水灾、瘟疫这些未来可能出现的灾难外,最现实的就是大旱,新疆那边目前没有受到影响。
朝廷想要百姓开荒,那总得先提供粮食,总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吧,如此算下来至少在未来的一年内,他们都不会饿着肚子的。
如此就行了。
这就是百姓们自己的一套逻辑。
明诏上规定的布政司的各个衙门都挤满了百姓,从社学抽调的学生、讲师们以及衙门的六房胥吏们将笔杆子抡的快冒烟了。
从百姓聚集到登记结束,仅仅只用了一个时辰的时间,更远处还有大量百姓汇聚而来。
看着一条条从县衙门口延伸到了更远处的长龙,官员们即是开心又是担心。
开心的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任务,虽然朝廷没有定标准,但这就是政绩,担心的是聚集的百姓太多了,可名额已经没有了。
“名额已经够了,都不用再排队了!”
“朝廷根据各个县的耕地面积、人口数量等等给予一定的名额,少则五百,多则两三千,我们县的名额是八百人。”
“目前已经登记了一千五百人,初步的名单我们马上会张贴在衙门外和菜市口的告示栏中,排在前面也不一定就一定会路上,后面的也不一定录不上,具体名单三天后公布。
整个过程都在锦衣卫的监督之下,绝对没有弄虚作假的可能。”
“如果前八百人都符合迁移标准,那么从八百零一之后的都将自动落榜!”
“诸位父老乡亲可以来监督,也欢迎大家伙儿来举报!”
“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第一次迁移中南半岛你们没赶上,第二次迁移乌斯藏你们也没有赶上,这一次迁移到新疆你们依旧没有赶上,诸位就要想想为什么了。”
“最后,本官多说一句,不要闹事儿,后果很严重!”
“行了,都散了吧!”
官员说完后便进了县衙,而胥吏们则是在锦衣卫的监督下将笔墨未干的纸张贴在了告示栏上,然后又迅速的抄录着,准备留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