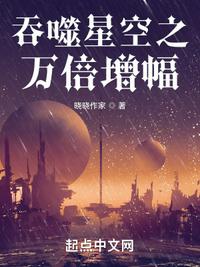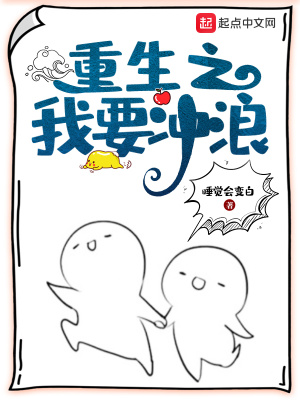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凤谋金台牛人全文阅读最新章节 > 120130(第35页)
120130(第35页)
他脑中想起前几日徐圭。她衣袖微扬,语气不急不缓:“我们不能只管眼前一年、两年的渔获,人能靠海吃饭。”
“但是,眼下百姓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前朝的规定已不适现在的情况,所以晋王府,晋王决定插手,修改捕鱼量的限制数额……”
那时,,未置一词。
大伙儿都觉得是好事,会离开,日后出了事也和她无关,那也是新官的事了。
百姓们渐渐散去,有的提着鱼筐,有的拉着船绳,重新投入生计。
天光斜照在潮湿的海面上,泛出一层金色,。
魏叔佑的事,也终于有了结局。
虽然他被革职,但因多年来的善政,以及在这场风波中主动配合、揭发幕后,他没有被流放,而是贬为庶民,暂时不得再任公职。
徐圭言说:“有错便该惩,有功亦不可抹杀。”这话传到百姓耳中,也算以德服人。
新的县令已在路上,听说是从监察司那边调来的清正之人,擅查贪案,也识政事。不少人暗暗松了口气,这场风波若就此平息,也不算白白经历。
然而,秦斯礼站在高处,看着海岸线那一幢尚未被收缴的豪宅,那是魏家侄子留下的“烂账”之一。
花檐朱栏、琉璃瓦顶,宛若误坠凡尘的宫殿。此刻孤零零地立在崖上,在夕阳下竟有些荒诞。
长安的早春仍带着几分寒冷,宫中花木尚未复苏,但局势流转却比任何季节都要炽热。
李起凡自晨起御前禀报开始,便心烦意乱。
有人把晋王李起年于岭南协同朝廷官员赈灾、处理魏县令之事的风声带回京中,传得沸沸扬觞。
李起年硬握官权,不惜牺牲地方官名声以维护清赈公正。
有人私下嘀咕:“趋正不趋权”,但“权者即正”的道理,说到底还是会被长安权贵理解为忤主之意。
可李鸾徽对李起年的处理夸赞不已,仁厚爱民,处理得当。
李起凡跟着应和,心中却危机感十足。
近些年李起凡被召回长安,协政圣上,同圣上商讨国事,可李鸾徽一直都没有立太子的意思,前些日子又点名了他们三人,李起凡心中说不出的气。
这么些年,他以为父皇在考察他,到头来还是要和六弟、十弟竞争。
这口气李起凡咽了下去,只是立储之事,也不光李鸾徽一个人决定,他肯定会问李文韬,该如何选择的。
好在,御前禀报这一番事迹的时候,李文韬的态度十分微妙,散会后,李起凡跟着他走了出去。
“李御史,您今儿精神不错。”
李文韬斜睨了一眼李起凡,停下脚步恭敬地行礼,而后缓慢地转直起身子,轻咳了几声,“大皇子,臣这身子是一日不如一日了,勉强活着罢了。”
“哪里的话,您定会长命百岁的,”李起凡笑着说。
“臣能过活一日,便为朝廷卖命一日,周王您有事要和臣说?”李文韬当然知道李起凡找他来是做什么的,李文韬三朝元老,早已混成人精,对面人呼出口他都知道开口要说什么话。
李起凡有点不好意思,左右看了看后说,“只是感叹十弟的优秀,岭南多灾多难,他竟然有如此成就,真是不容小觑……”
李文韬笑着点点头,“你们都是圣上的皇子,自然都有圣上的魄力,圣上的能力,这不足为奇。”
听这话的意思是说他监国成绩也还不错?李起凡干笑一声,“我实在是佩服十弟,此等功绩,被当地百姓口口传颂,真是人才辈出。”
李文韬笑着点头,不再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