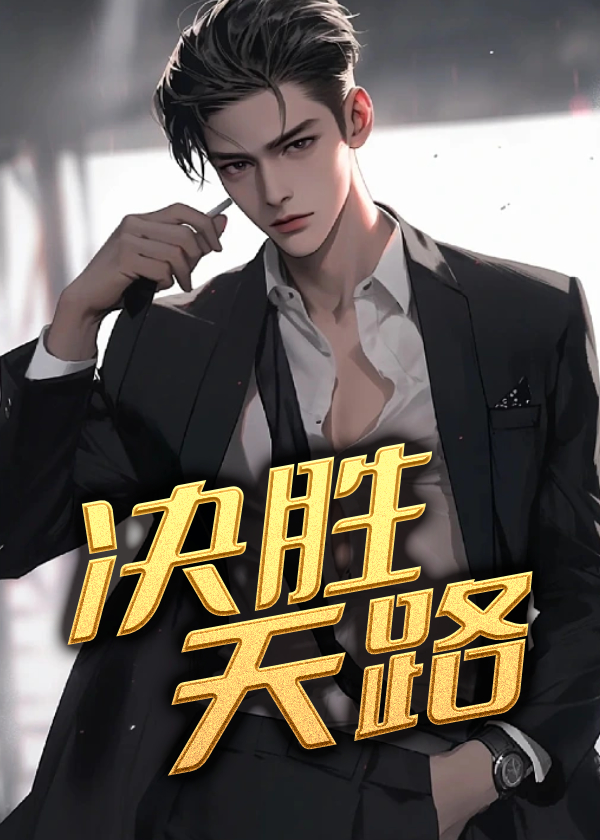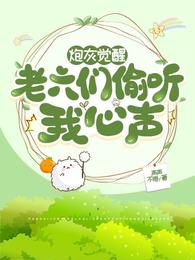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凤谋金台牛人全文阅读最新章节 > 130140(第16页)
130140(第16页)
问秦斯礼,他在长安多年,自然是清楚朝廷内党派的情况,可他什么都不说,她是什么都问不出来。
事发突然,秦斯礼也不清楚怎么一回事,现在朝廷内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圣上和李文韬,两人各占一势,牛和德前些年因为贪污被贬了官,圣上也没再扶持一个同李文韬打擂台的人。
一年年看下来,圣上当年没有一鼓作气搞掉李文韬,是个大错误,导致他总是被李文韬他一头,这也正常,李文韬是二朝元老了,外面人称半仙,是比人精还精的“仙”。
这次立太子,看似是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平衡,但实际上,立太子一事本就是圣上说了算,李文韬不会踩这条底线和李鸾徽叫板的。
况且,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二位皇子,只有周王是储君预备役,没人会做这等蠢事。
秦斯礼徐圭言两人坐在车中,各有所思,各怀鬼胎,表面上和睦相处,实际互相算计,她套话,他装傻。他打量,她躺平。
离长安城越近,两人之间的猜忌越发得多。
说来也有趣,长安似乎有一层魔力,徐圭言原本淡忘的记忆在回程路上一点一点地回到她身边。
身份、职责、过往的恩怨和未竟的因果会一齐涌来,正因如此,她与秦斯礼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他们是御前党争的棋子,是旁人眼里不该有任何瓜葛的男女。
“长安鱼龙混杂,可不是你一两句就可以打探清楚的,”秦斯礼放下书,给自己斟了一杯茶,不紧不慢地喝了起来。
看秦斯礼这神态,似乎是嫌弃徐圭言早已不明朝廷内的情况,这分明就是把她当乡巴佬了。
徐圭言看了他一眼,低声笑了一下,靠回软垫,不再多言。
马车继续驶向长安。
尘埃在日光中翻腾如雪,光影交错。
五日后,
李起年回到长安,心中十分忐忑,,可对长安的记忆只停留在后,还有一路的奔波。
跟在他身旁好奇,但也有些胆怯,这是她长这么大第一次来到后唐的中心,小心翼
好在李起年对她足够照顾,入宫礼仪都由他亲自讲解,嬷嬷之前告诉过她,可真真到了太极殿前,她紧张得什么都忘了。
说到李起年,在成婚前,沈溪龄对他知之甚少。
十皇子,贬至岭南,远离中枢,即便赐了“晋王”封号,世人也知道,这不过。
陛下的这位幼子,从未在京城站稳过脚,十岁那年便被送来岭南,说是封蕃做王实则是个被放弃的皇子——沈溪龄也是在偶尔听父亲与朝中同僚闲谈时,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李家骨血”。
那时,她尚未及笄,只记得父亲淡淡地说:“此子运衰,陛下不欲他久留。”
再往后,便是数年无闻,李起年的名字如一缕微尘,沉入京师庙堂的波涛中。在岭南,也不过是一个摆设摆了。
沈溪龄真正对这个名字有印象,是在婚期前后。她身为沈家独女,从小锦衣玉食长大,晋王府长史徐圭言上门求亲,晋王的婚事,没有几家敢反对的,她的父亲沉默了许久。
“晋王如今也是王。”外祖母说得含蓄,语意不明,“嫁过去,你要好生过日子。”
沈溪龄不是不通世事的闺中女子,她懂得这桩婚事背后的含义,她始终觉得这桩婚事是为了父亲的仕途。
她没见过李起年,也不知他容貌性情。
她曾以为,他们的婚后生活,会像两尊被放置在檀木案上的人偶,相敬如宾,各自沉默。
可成婚之后,一切却又不如她想象。
成婚那日,京中派了使节监督,仪制虽不华贵,但也一应俱全。
她第一次真正打量李起年,是在拜堂后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