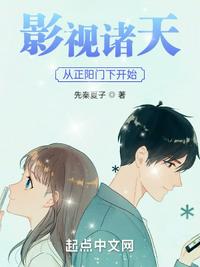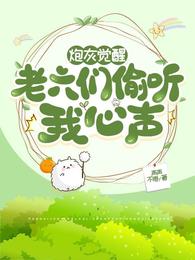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凤谋金台牛人笔趣阁 > 140150(第17页)
140150(第17页)
史官见他们盯住刘通之名,轻轻一叹:“此人……突然被调去隶属护军,之后死于营中‘误伤’,葬于军墓。无人敢问。”
三人面色皆变。
与此同时,另一队人进入大理寺后堂,翻出当年卷宗。
翻至结案之页时,一人轻声说道:“奇怪,此案结尾不是御前对质,不是廷辩,而是——由刑部判官代签结案,皇命只见一道旨意,并无口谕。”
大理寺属官疑惑接道:“照理如此等大案,应有廷推审议……为何会跳过程序?”
“我们倒着查。”秦斯礼手下之人语声沉稳:“从结案那一刻往前推,看看有无改动痕迹。”
果然,他们找到一页用纸不同、字迹异样的供词。仔细对照发现,供词中有一名关键人物——内廷掌印太监林永寿——此人在供词中出现频繁,但在结案文书中被删得干干净净。
“林永寿……”大理寺丞低声念叨,“此人后升为内监监正,三年前暴毙,圣上亲自赐殡。竟然是旧案中人?”
三人相视,气氛愈发凝重。
傍晚,众人回府复命,秦斯礼听完后没有说话,只在烛下展开两份笔录,沉思良久。
第二日,正午时分,长安宫城深处,重帷低垂,水汽氤氲。殿中香汤袅袅,沉檀清雅,细竹帘外侍人屏息伺候,不敢有丝毫声响。
殿内,一池温泉泛起微波,圣上李鸾徽斜倚于檀香木的澡榻上,肩背微露,鬓角湿润。他闭目不语,任由水面浮光流转,一如心绪。
一旁掌浴的内侍名唤文昭,是李鸾徽少年时便随侍左右的老人,虽为宦官,却沉稳老练、识人精明,深得圣心,几乎可在旁随意言语。
文昭正为圣上轻柔地搓洗肩背,低声道:“陛下,秦大人查案一事,如今已传遍长安了。说他日日不出秦府,就是为了整顿旧案,一笔一笔翻得极细。连御史台、国史馆的人都日日去回,快成新热闹了。”
李鸾徽睁开眼,看着水面,语气未变:“沸沸扬扬,是他惯有的作风。”
文昭叹道:“旧太子可惜啊,当年那事出了,宫里宫外,谁不知旧太子出事后,下一个太子必然是周王。可那时谁敢说?人人闭口,个个装傻。说是谋反……其实不过是借机除宇文家。陛下,太子是您亲封的,怎会轻易谋逆?”
圣上微微偏头,眼中浮现淡淡寒意,看向铜镜倒影中那张老去却忠诚的面孔,缓缓反问:“你也看出来了?”
文昭不慌不忙,将毛巾拧干,语声低而笃定:“圣上,老奴陪您多少年了?太子立废、朝局波动,那些门道……奴才也不是看不懂。太子虽非圣后所出,却由她抚养多年。他若真有异心,老奴第一个不信。”
他停了停,望着李鸾徽的发顶,忽地轻叹一声:“陛下,您这头发里……白的多了。”
李鸾徽闻言,愣了片刻,抬手触了触鬓角,竟觉指尖冰凉。他没有开口,半晌后才低声喃喃:“周王是朕的儿子,朕最爱他。他聪明,有气度,有锋芒……若无这些,朕如何肯把他放到储君之外?可若只有这些,如何承大统?”
他靠回榻上,眉间隐有倦意:“爱之深,责之切。朕不会亏待他,也不会无谋他前路。他若稳得住,朕自然会给他最好的。他……急什么?”
文昭将干巾搭在他肩上,低低应了一声:“是啊,他急什么呢。”
殿外风声拂动,传来远处宫人报时的鼓声,恍若惊涛暗涌。
日头初上,朱雀街的雾尚未散尽,官道之上车马来往,徐府内却一片静寂。
徐圭言坐在偏院书斋中,桌上摊开的是密探送来的画像——据说是“太子旧案”中参与镇压的禁军士卒,如今已归于周王麾下,正是他出面作证,说太子夜间翻墙召党,宫中起火皆属谋反之象,且声称亲眼所见。
她细细端详画像,眉头越蹙越紧。
那人中等身材,颧骨略高,左眉上方有一道细痕,画像下方还附了一行小字:“曾为镇南卫副尉,后调隶于周王营下,现于邠州。”
她将画像与脑中记忆对照,不禁低声自语:“不对……此人我见过。”
那日破门而入,秦斯礼带着一群人来抓她,那人群中正巧有此人。
现在这人却说他去抓了前太子,这不是胡扯呢么?
秦斯礼不记得了?他记性这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