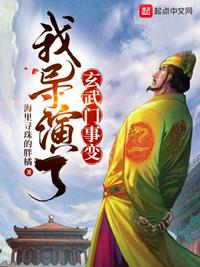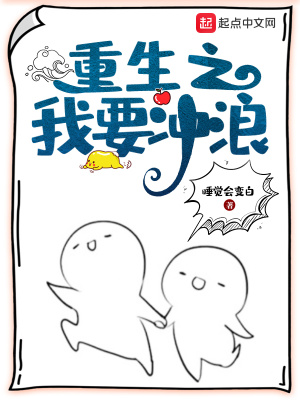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凤谋金台牛人免费阅读 > 150160(第19页)
150160(第19页)
两人落座,中间隔着一张乌木案。徐圭言坐得不卑不亢,姿态不显咄咄,却稳如老松。梁念瑾看着她,不禁出神。
“这些年没见,您倒是……一点都没变。”他说着,勾了勾唇,神情倒不像刚才那样冷。
“我倒觉得将军变了不少。”徐圭言回应,语气不咸不淡。
两人四目相对,各自沉着,各怀心事。
梁念瑾一笑,抬手招呼茶童上茶,略带调侃:“您大人有大量,当年在凉州的时候,是带着我们立的功。那时我太年轻了,许多事不知轻重,若有得罪,还望您不记。”
这话里的意思太明显了——你我交情不深,如此上门来找我,是为了什么事?叙旧?我是不信的,我们之间,没有旧情需要叙。
徐圭言微微一顿,眼角的笑意收了些。
她喝了口茶,又看了他一眼,略一侧首,似是认真地审视,然后不再绕弯子,径直道:“边疆战乱时常有的事,现在善于都护府那边也是非常忙吧?你是那边的主将之一,如今回朝,不说旁的,边境百姓的日子……该如何过?”
梁念瑾闻言,嘴角动了动,笑了一声:“哦,原来是问这个。”他放下茶盏,语调轻松了些,“您放心,大部队都在,契丹人不敢造次。善于那边,稳得很。”
徐圭言听罢,淡淡一笑,低头轻啜一口茶,随后抬眼望他,笑意未达眼底:“梁将军,这话哄旁人还成,哄我可不行。军营中的事,我不说通晓,也算熟得很。您身边那支精锐是跟着您回来的吧?主心骨不在,士气先散了。战场打得是什么?打的是胆气,是气势。您以为留下的人能顶住?能保护好百姓?”
梁念瑾眼神沉了下去,望着她,没有马上答话。他盯了她几秒,才道:“圣上让我回来,是有原因的。我这人听命行事,回不回都由陛下裁决。您是晋王府的长史,边地之事,恐怕……不归您管。若手伸得太长,既不好看,对您,也对晋王,不好。”
他这话说得温吞,实则句句带刺。
徐圭言的脸色也沉了几分,慢慢放下茶盏,目光稳稳地看着他:“官场的弯弯绕绕我不想说,你也别和我来这一套。我今日来,是关心边民百姓,不是干涉兵事。”
梁念瑾也坐直了,语气渐冷:“既然如此,我也不说场面话。”
他顿了顿,冷静地说道:“为了大多数人的安稳,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这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您想啊,有五个下等兵被抓了,您会出兵几千去救他们吗?出兵,死的就不止五个;不出,损失只是五个。这不是我们这些人日日在权衡的事吗?”
说到这,他忽然冷笑了一声,语气微讽:“您是许久没在战场上,忘了这个道理了吧?就算出了事,朝廷会赏银,会抚恤,有这些安抚金,对百姓而言更实在。”
徐圭言盯着他的脸,眉心轻蹙,心中一动:几年不见,各有各的长进……
她缓缓道:“我们讨论的不是五个人和五千人的事,我们讨论的,是一个人,和一个州的人。”
梁念瑾几乎是下意识地回了一句:
“九五至尊,是普通百姓能比的吗?”
这句话一出口,两人同时沉默了。
徐圭言的脸色变了又变。
梁念瑾也不想继续做姿态了,反而往前倾了倾身子,语气也冷了下来:“圣上不好战,后唐如今除了边疆,其他地方皆是国泰民安。无人敢说他不是明君。部分地区战乱,换来更多地方的太平——他们,是解决问题的最小成本。”
徐圭言坐着,良久,长长呼出一口气。
她没再说话。那一刻,她忽然明白,有些人是在风雪中磨出了锋刃,也磨掉了心。
直到告辞时,梁念瑾送她出门,一路送到门外,门前两盏红灯被风吹得斜斜晃动,像将要熄灭。
他站在台阶上,背着光,语气平静却透着某种警告:“徐长史,你我都是为圣上做事的。”
“但现在,你……似乎搞错了对象。”
“你这个‘长史’,是圣上给的。”
他说到这儿,略顿,露出一点点笑意,那笑意里没有体谅,只有锋利:“做官,要时时牵挂百姓没错,但他们能给你的,也只是个‘好口碑’。”
“可好口碑,能让你升官吗?能让你从阶下囚成为徐长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