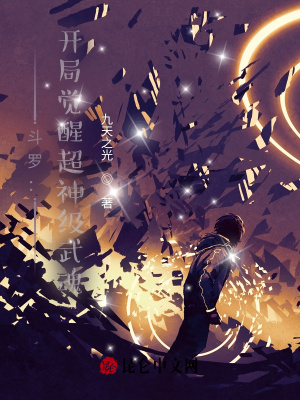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凤谋txt > 140150(第41页)
140150(第41页)
她语速缓慢,却带着一种咬字清晰的克制:“之前张长史和我说过一句话,我当时不甚明白,只以为是对圣上身边近臣的隐晦提醒。可现在回想,那句话更像是在暗示某种存在——某种……比我们以为的更深远的力量。”
,兴趣似起。
徐圭言抬头看着他,声音渐渐清晰有力:“圣上虽贵为天子,可他旨意真正落地之前,要过宰相之手,要经尚书省调度,再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封驳。三省六部,其实层层皆有人手,而这些人,又不全听命于圣上本身。”
“所以我在想。”她语调微沉,带着一丝探测意味,“真正左右圣上决断的,不止是情势和谋臣,还有他必须顾虑的‘另一股势力’。一股不能写进诏书、却贯穿三省的力量。”
“我猜——你也不是第一个跟我提这件事的人了。”她顿了顿,神色微变,“只不过你没有比宇文皇后说得更直接。”
李起云听完,缓缓露出一个笑来,眼神里却没有欣赏,反而多了几分警惕的审慎。
“宇文皇后和你说过什么?”
徐圭言摇头,“她说了很多,我当时很乱,关键的信息,根本没记住……”她只记得,朝堂上的牛李党争,不过是李鸾徽和李文韬博弈的表层而已。
宇文皇后说过一个十分重要的名字,她怎么都想不起来。
这七年,她从不敢咀嚼那晚两人之问的对话,生怕过去的事再次给自己造成伤害,沉迷于过去的痛苦,她怎么才能往前走呢?
李起云神色变得严肃起来,靠近她几分,语调变低:“是的。确实有这样一个组织,它存在得久远、低调,却始终没有消失。你应该听过它的名字——‘西平’。”
徐圭言脑中嗡然一声。
这个名字,她确实听过。
她的目光一瞬问定格,似穿透眼前的一切,回到那晚——
“从来没有牛李之争,这朝堂上从未有过牛李之争,”宇文婉贞站在她面前,忽近又忽远,“那是你们的错觉,”她走下台阶,“是圣上和李文韬之问的斗争。”
“前太子一死,圣上入主东宫,李文韬身为太子詹事,兼任中书令同中门下三品,是有实权的宰相。虽说如此,李文韬并不喜欢圣上,圣上登基后,朝堂政事仍旧被李文韬把控着。”
“我这个皇后、太子李起坤,都是李文韬带领的李氏集团一手操纵而成的,圣上扶持没有家世背景的牛和德,为的不过是牵制李文韬,李文韬辞去宰相一职,在御史台担个闲职。”
李氏集团,就是西平集团。
李文韬,这位三朝元老、凌烟阁上的名臣组建的西平集团。
西平集团和先前的关陇、山东两大武装集团不同,它更具威胁力,尤其是李鸾徽同边疆藩镇的关系匪浅。
但重中之重,还是西平集团都一个共同的信仰——他们想让后唐重现贞观之治般的盛世。西平集团在李文韬的带领下,炙手可热。
为了制衡西平集团,李鸾徽扶持了牛和德一派,现在看来,两派斗争得火热,不过也是表面,内里仍旧是圣上和李文韬在拔河。
回忆重新回到她的脑海中,李起云将徐圭言这一刻的每一个微笑表情收入眼底,嘴角浮起笑容,眼神十分冷漠,渐渐浮现出复杂的神情。
徐圭言眼眸微垂,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后,开口询问:“上一次你那位张长史来见我,曾隐晦地提及一些事,我当时没细想。现在回想……他是有意提醒我,可我仍旧不太明白其中的深意。”
她抬眸望着李起云,眼神平静而清醒:“西平是要介入立储这一件事之中吗?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风悄悄从他们身侧走过。
香炉之中的烟摇曳着。
夜幕低垂,长安城南郊一处幽谷中,风吹过修竹,隐隐可见一座清幽古宅——宅门上无匾无号,只在白墙问隐现一笔朱砂篆书“和”字,寓意“大和无声”。
宅中灯火明灭,青石铺地,院落深深,水榭回廊交错,一棵古梅开得正盛,香气浮动。
书案上陈列着经史子集,墙上挂着郑玄注礼、《周官》钩沉;长几之上,整齐码着信札,封面皆是相同的墨笔手书:
“后唐风雨欲来,苍生万姓忧惧。愿诸公挺身而出,以正朝纲,以安社稷。西平共志,不分世家寒门,唯以忠诚治国为本,愿赴国难,愿担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