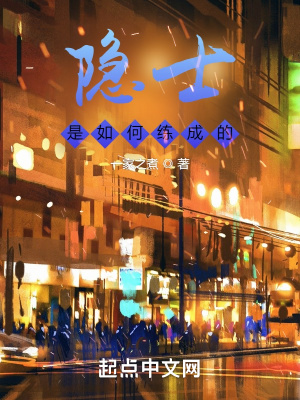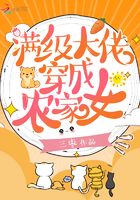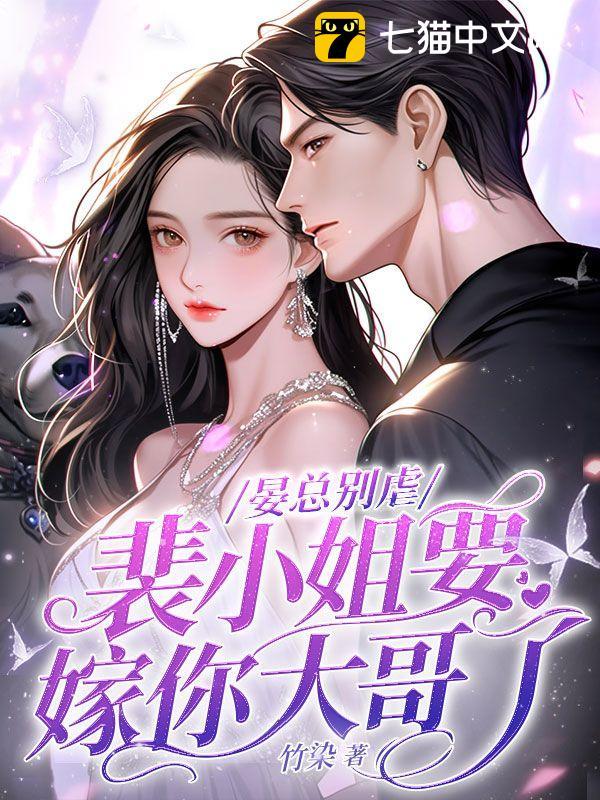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问鼎从一等功臣到权力巅峰无弹窗 > 第2465章 黑中介(第1页)
第2465章 黑中介(第1页)
棠下村北入口的小巷,窄得像被两座民房挤出来的缝隙,三月底的晨光斜斜地从屋顶瓦片间漏下来,在青石板路上投下细碎的光影。
沈青云刚踏进巷口,一股混杂着热豆浆香气、油条油烟味和老房子潮湿霉味的气息就裹了上来。
这是城中村特有的味道,鲜活又带着点杂乱,和省厅办公室里的茶香截然不同。
他放慢脚步,目光扫过两侧的民房。
大多是两层的红砖小楼,墙面上被各种广告贴得密密麻麻,红色的“招工”、蓝色的“租房”、白色的“办证”字样层层叠叠,有些广告纸边角卷翘,露出底下更早的字迹,像一层层剥落的树皮。
最扎眼的是几张用黑色马克笔写的小广告,歪歪扭扭地写着“无抵押贷款,当天放款”和“代开假证,保真可用”,贴在电表箱上,格外刺眼。
“省长,前面有个早餐摊,人不少。”
刘福荣压低声音,指了指前方对沈青云说道。
沈青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巷口十米远的地方,一个蓝色的帆布棚子支在墙边,棚子下摆着两个煤炉,一个煮着豆浆,咕嘟咕嘟冒着白气,另一个炸着油条,金黄的油花溅起,香气飘出老远。
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头发用黑色发网包着,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围裙,手里握着一双半米长的竹筷,正不停地翻搅着油锅里的油条,额头上渗着细汗。
摊位前围了七八个人,有穿着藏青色工装的年轻人,袖口沾着机油,手里捏着手机,一边等油条一边刷短视频。
有背着粉色书包的小女孩,被奶奶拉着,踮着脚盯着油条,嘴角亮晶晶的。
还有个提着竹编菜篮的老太太,菜篮里装着几颗青菜,正跟阿姨讨价还价,说“昨天的豆浆稀了点,今天可得多给点豆子”。
几个半大的孩子在摊位旁边追逐打闹,手里拿着塑料弹弓,石子儿在地上滚来滚去。
看到沈青云、刘福荣和周朝先三个陌生面孔,他们停下来,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了几秒,其中一个胖小子还对着周朝先做了个鬼脸,然后又笑着跑开了,脚步声在窄巷里咚咚响。
“就从这儿切入。”
沈青云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刘福荣,眼神示意他先上。
刘福荣会意,把背包往身后挪了挪,快步走到早餐摊前,脸上堆起憨厚的笑,像个刚从老家来的年轻人:“阿姨,麻烦来碗豆浆,两根油条,要现炸的。”
阿姨抬头看了他一眼,声音洪亮:“好嘞!豆浆要甜的还是咸的?我们家甜豆浆放的是红糖,比白糖香!”
“甜的,谢谢阿姨。”
刘福荣接过阿姨递来的搪瓷碗,碗沿还带着点温度,他吹了吹热气,喝了一口,然后装作不经意地叹了口气,“阿姨,跟您打听个事呗,我刚从老家来,想找个电子厂的活干,看墙上贴了不少招工广告,说月薪五千还包吃住,可我老家的人说,这边黑中介多,收了押金就跑,我心里没底,不敢随便信。”
阿姨手里的竹筷顿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警惕,然后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用带着羊城口音的方言说:“小伙子,你可别傻!那些贴在墙上的招工广告,十个有九个是骗子!上个月有个外地的小伙子,跟你一样,刚从老家来,看到广告上写电子厂招普工,月薪六千,就找过去,那中介让他交三千块押金,说怕他干几天就跑,结果第二天小伙子再去,中介的门都锁了,电话也打不通。”
她叹了口气,用竹筷指了指墙面上一张招工广告:“你看那张,写着电子厂直招,其实就是那个姓王的中介贴的,他都骗了好几个了!小伙子你要是真想找活,就去村东头的劳务市场,那边有正规的中介,虽然月薪就四千多,但不骗钱,还能跟厂里签合同,有保障。”
刘福荣眼睛一亮,连忙追问:“阿姨,劳务市场好找吗?具体怎么走啊?我路痴,怕走丢了。”
“好走!”
阿姨放下竹筷,用手比划着:“你顺着这条巷一直走,过两个红绿灯,到第三个路口左拐,就能看到一个蓝色的牌子,上面写着棠下村劳务市场,早上八点到十点人最多,你现在去正好,晚了好活就被别人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