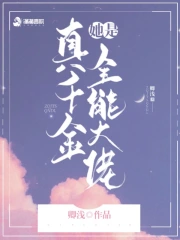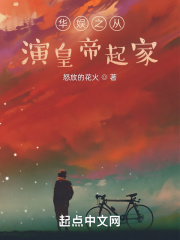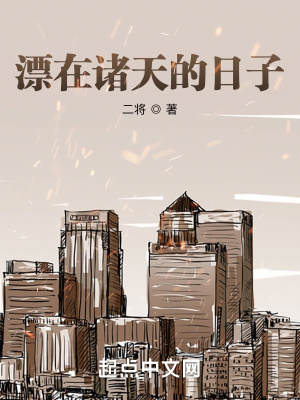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末世两界倒爷正版 > 第1556章 粗糙制品(第1页)
第1556章 粗糙制品(第1页)
冯俊的脚步在“开拓者号”庞大而幽暗的舰体内部回响,每一步都踏在覆盖着薄霜和金属碎屑的甲板上,发出清晰而孤寂的声音。与他曾在至高天惊鸿一瞥、意识体踏入过的“新五月花号”那充满美式实用主义未来感的内部截然不同,这艘苏维埃巨舰的内部构造呈现出一种独属于那个红色帝国的、近乎歌剧式的宏伟与狂想。
“新五月花号”的内部,是标准化的高效与冷峻:笔直宽阔的通道,棱角分明的舱壁,整齐划一的嵌入式设备接口,所有管线都被精心收纳在壁板之后,照明系统提供着均匀、无影的冷白光,一切都为功能服务,透着一股硅谷精英式的、剥离了冗余情感的极简主义未来感。
而“开拓者号”,则是一座钢铁铸就的巴别塔。它的主通道宽阔得足以让重型卡车并行,拱形的穹顶高悬在上方,仿佛某种宗教殿堂的廊道。舱壁并非简单的平面,而是呈现出优美的流线型弧度,表面覆盖着带有细微纹理的合金板材,既是为了在长期太空航行中对抗金属疲劳,也透着一丝不合时宜的、对“形式美”的追求。照明并非均匀散布,而是由一系列镶嵌在舱壁和穹顶上的、带有华丽金属罩的大型灯盘提供,散发出偏暖色调的、略显昏暗的光芒,在巨大的空间中投下片片阴影,营造出一种既庄严又压抑的氛围。
巨大的、包裹着隔热材料的管道和线束并非完全隐藏,而是如同巨树的根系般,沿着舱壁虬结盘绕,暴露在视野中,彰显着一种粗犷的、毫不掩饰的工业力量感。这里的一切,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民族试图将大地上的集体主义荣光与对未来的浪漫狂想,一同塞进这钢铁方舟,带往星海的彼岸。
--------------------------------------
冯俊并非漫无目的地探索这片钢铁迷宫。他的行动精准而高效,如同一个融入阴影的猎手。他没有释放大范围的侦查无人机或纳米蜂群,那会打草惊蛇。取而代之的,是数只仅有手指粗细、通体哑光黑的机械蠕虫被他悄无声息地释放而出,如同拥有生命般贴地疾行,以远超肉眼捕捉的速度没入前方的黑暗之中。它们是他延伸出去的感官,沿着几条通往舰船核心动力区域的预设路径进行快速扫描,将前方的地形数据、能量读数以及微小的震动反馈实时传递回他的战术目镜上。
他的行进方向明确——朝着那股低沉、隐晦、却如同黑洞般吸引着他感知的至高天能量反应源头,也就是巨舰的引擎核心区域,稳步推进。
凌玖的失联是他心头最重的疑虑。作为他麾下至关重要的高级人工智能,凌玖的本质并非仅仅依赖于那具生物躯体。她的核心意识应该深植于新上青市地下深处、来站前明帝国科学家打造的超级量子计算阵列之中,通过几乎无法被常规手段干扰的量子纠缠网络与所有分身保持即时同步。
理论上,即使这具进入开拓者号内部的生物载体被彻底摧毁,凌玖她也最多是损失了一个高级终端,其主意识根本不应受到影响,更不用说出现这种诡异的、仿佛被“割裂”和“剥离”的断联。
----------------------------------------------------
然而,这不可能发生的事,偏偏发生了。根据工程师对凌玖本体的紧急检测报告,位于避难所地下的量子计算阵列硬件毫无损伤,但其内部负责运行凌玖主体人格逻辑层、情感模拟模块以及高阶决策算法的庞大程序集群,却近乎完全陷入了停滞状态,仿佛突然失去了最核心的驱动指令。阵列仍在运行,却只剩下一些基础的、机械性的应答功能,退化成了一个空洞的shell,一个失去了灵魂的躯壳。
所有的数据波动都指向一个惊悚的事实:在开拓者号内部的生物载体失联的同一微秒,某种东西跨越了物理距离和量子加密协议,直接“夺走”或“隔绝”了凌玖那本应无处不在的意识核心。
这种手段,已经超出了冯俊对现有科技,甚至是对一般至高天力量的理解。这让他心中的警惕提升到了最高等级。
进入靠近动力传动区域的宽阔甲板层后,环境开始变得愈发诡异。冯俊遭遇了一些零星出现的、堪称“原始”的自动防御单位。它们与其说是机器人,不如说是一堆被无形力量勉强粘合在一起的破铜烂铁:锈蚀的金属板用粗糙的焊接和扭曲的线缆胡乱拼接成人形或蜘蛛形,关节处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行动迟缓而笨拙。它们的“感知”系统似乎极其落后,往往等到冯俊几乎走到面前才有所反应,挥舞着焊接着金属条的手臂踉跄冲来。
冯俊甚至懒得动用链锯剑,只是用爆弹手枪精准的点射,沉重的爆弹便轻易地将这些简陋的构装体炸成一堆四散飞溅的零件。他甚至用军靴踩碎了一个仍在抽搐的金属头颅,其内部暴露出的只有最基础的磁力线圈、老旧的继电器和杂乱无章的铜线,找不到任何类似中央处理器、数据总线或哪怕是稍微复杂一点的逻辑电路的痕迹。这些东西,更像是一种…被某种力量强行驱动起来的金属玩偶,而非真正的自动化防御机器人。
它们显然不是凌玖报告中提到的、那些能与第五军团侦察兵交火的“难缠”的敌人。这些破烂玩意儿,充其量只是外围的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