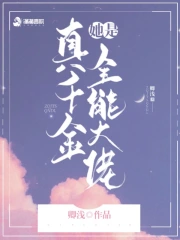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回档换个姿势再来一次无防盗 > 第1558章 风将起浪要至(第1页)
第1558章 风将起浪要至(第1页)
紫菜蛋花汤的蛋花还未散开,那辆庞大的林肯领航员已无声地停在榕树稀疏的荫影边缘。
车门打开,先下来一个穿着黑色衬衫,留着板寸精壮汉子,四周扫视一圈,拉开后座门。
一个身影弯身而出,四十多岁,中等个头,清瘦。熨帖得一丝不苟的浅灰色棉麻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略显苍白的手腕,腕上戴着一块看不清牌子的手表。
鼻梁上架着一副半框黑边眼镜,镜片后的眼睛不大,眼神温和,甚至带了点腼腆与书卷气。
头发梳得整齐,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倒是让人一见便生出几分亲近感。
这形象,与李乐脑中预想的那种草莽形象的“响哥”或是掌控着和信达网络的“大天二”相去甚远,更像是一位教书匠,甚至是十几年后,哪家公司被当做牛马压榨,依旧为了一口吃的和妻儿老小,忍辱负重挣着那点窝囊费的社畜头目。
两人走进来时,饭馆里原本嘈杂的本村食客声音都低了几分,不少人目光瞟向门口,带着敬畏或好奇。
也有“响仔”、“响哥”、“阿标”,打着招呼的声音响起。
男人不断点着头,应和着,“六公,不在家吃啊?”
“宝哥,下午有空来家,后院铁门门栓脱焊了,帮忙焊一下。”
“满意,大中午的就这么喝,不怕回家又打架?”
男人目光扫过店内,很快落在梅苹这一桌,脸上笑容更盛,径直走了过来。
“打扰各位老师同学用餐了,”标准的闽普,但透着股斯文,“我叫陈言响,就住在村里。听阿旺说,燕京来了大学者到我们这小地方做田野调查,想着,怎么也要来问候一声。”
他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在气质最为突出的梅苹身上,表情真诚而略带谦恭,仿佛真的只是来尽地主之谊。
梅苹放下汤匙,站起身,脸上是恰到好处的客气,伸出手,“陈先生太客气了,我是梅苹,人大的社会学副教授,课题组的负责人。这几位都是我的学生和同事。”
“我们只是做些基础的社会调查,倒是打扰乡亲们了。”
陈言响和梅苹的指尖略一触,便收回手,“梅教授才客气,什么先生不先生,叫我阿响或者直呼其名。在您这样的大学问家面前,我,就是个粗人。”
说着,目光扫过桌上其他人,在蔡东照身上略作停顿,点了点头,似乎认识,等最后落在李乐身上,一瞬间愣了愣,又忙看向梅苹。
“粗人可不敢当,”梅苹微微一笑,语气平和,但透着股疏离,“听闻陈先生在村里口碑极好,造福乡梓,本来还想着请陈老师出面,和陈先生聊一聊的。”
“好,好,随时都行,欢迎,欢迎。坐,坐着说。”
陈言响拉过一张空凳子坐下,那个板寸壮汉,则无声地退到门口,抱着胳膊站定,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周围。
“听永泰公说了,梅教授这次来合口,搞的是国家的大课题吧?研究咱们这儿的宗族文化?”
“是的,”梅苹点点头,“一个关于乡村治理转型背景下宗族组织变迁的社科课题,主要是学术研究。”
“不过我们这次课题是纯粹的学术研究,重点在于观察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不涉及具体的经济活动或个人评价。”
“哦,学术研究好啊。”陈言响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显得很诚恳,“咱们闽南这边,宗族房头的老传统,根子深。现在时代变了,这些东西怎么变,怎么适应,确实值得好好研究研究。你们是专家,眼光准的很咧。”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桌上摊开的笔记本和资料,“上午在村里,听旺仔说你们在查些资料?怎么样,还顺利吗?村里这些老账本、旧记录,年头久了,乱七八糟的,怕是不好找吧?”
“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我在村里还有点薄面,跟几个房头的老叔公也说得上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