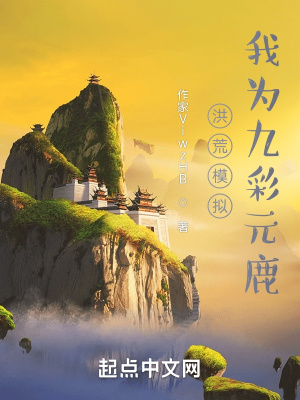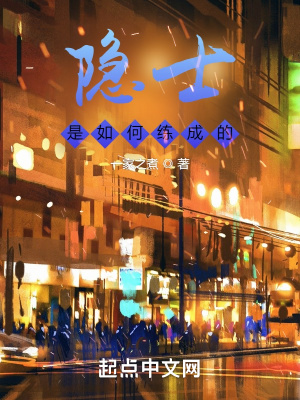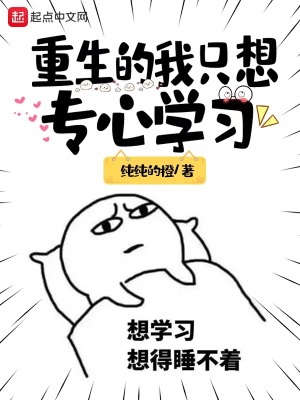四月天小说网>回档换个姿势再来一次无防盗 > 第1557章 这就是个吃货(第1页)
第1557章 这就是个吃货(第1页)
(肩膀疼,手麻了,就这么多吧,贴膏药去。题外话,戏台的编剧,怎么成了陈老师?瞎猜可能是毓钺老师觉得,你丫给我改成电影,还是写你的名儿吧,到时候丢人也丢你的,哈哈哈哈。。。。。。)
因为梅苹坚持,没能吃上村委会准备“便饭”让李乐颇有些遗憾。
五人挤在村口大榕树荫蔽下的一家小吃店里。
一张桌子油腻腻的,头顶吊扇嗡嗡转着,也搅不动多少凉风。
老板兼厨子是个精瘦老头,正颠着炒锅,灶火哔啷作响,混合着一股夹杂着蒜头、蚝油的香气。
“海蛎煎、炒花蛤、炒冬粉、蛏子炒娃娃菜,米酒蛋炒饭。。。。。”
蔡东照吆喝着,顺手用茶水烫洗着碗筷,发出刺啦声。
梅苹把一摞资料小心地放在脚边的圆凳上,用纸巾擦了擦额角的薄汗。
姬小雅对着小风扇猛吹,一边翻着数码相机里,李乐上午拍的照片。许言皱着眉头,试图把裤线在矮凳上抻平。
而李乐则盯着灶台方向,饶有兴致地看着老板利落地颠勺。
菜还没上齐,梅苹就开了口,“说说吧,上午两边的情况,都碰一下。”
一句话,让几人都看过来。
“先说我这边,主要是整理村里近些年的人口简报,结构信息,还有部分关于村集体事务以及经济活动的相关资料。。。。。村子的人口成分、相关比例、近些年增减变化。。。。。。”
“上述这些基本资料小雅这边会在今天晚上整理出来。。。。。我们陈厝村的经济账目、村集体活动的登记事项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
李乐这时候抬手,“诶,梅老师,您先别说,我们在村里做了几家的入户,也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咱们一起说,看看是不是一样。”
梅苹笑了笑,“行啊,那就。。。。。和信达!”
“陈言响!”
两人的异口不同声,让蔡东照“嗨~~~”了一声。
许言倒是说道,“这个,其实都一样。”
梅苹点点头,“对,通过登记的资料,能看出来那个和信达、陈言响或者叫陈达标的在陈厝的影子很深,捐路、建祠、发老人钱,甚至村里不少人在那打工。法人是几个族老,但实际操盘手,是这个公司。”
“陈旺主任说这是企业反哺,但反哺的路径很微妙。”
说着,从腿边的圆凳上,抽出几张复印件,递给许言和李乐,上面是模糊的签名和用红笔做的备注。
李乐瞅瞅,没说话,许言则是皱着眉,仔细翻看着,“我们在入户访谈也发现了端倪。村民提到急用钱,除了找亲戚,不少人都说可以找公司预支工资,我们以为指的就是和信达旗下的厂子。
“但是后来才知道,其实就是到宗祠那边,找一个叫陈猛甲的人,从族里拿钱,等到时候,按照比银行高百分之十的付息比例还钱,但签字的是一家叫和信达的典当行。”
“而问到村里谁说话管用,除了族老和干部,好几个都提了那位响哥,语气,听着也很自然。”
许言想了想,又带着点学术的严谨补充道,“这是一种非正式权威与正式经济组织的深度嵌套。反映了传统宗族权威与现代经济力量代表在村民生活,以及村务影响力上的交织甚至。。。。某种程度的融合。”
“李乐,你呢?”梅苹看过去。